
公开的秘密
一早,没听见尹队长的破锣嗓喊出早工,正感意外时,他笑眯眯的走进我们五个男知青住的抹角里,“男的今天都上义南闸挑堤去,两个女的留在队上出工,吃了早饭就走”尹队长对我们说,“锄头、扁担------都帮你们准备好了,放在郭贫协家(社员们对贫协组长的尊称)自己去拿,工具购置费在安家费里扣”。
我们背着被包,斜挎扁担,那地上的影子就像一队扛着汉阳造的红军战士,沿着晒满禾苋子草(社员叫瘪谷子稻穗为禾苋子草)的垸堤一路秋风一路歌的行进。“十送里格红军,介子个下了山------” 有幸出回集体工,一路上大家高兴得把会唱的歌与样板戏翻来复去地唱了好几遍。
在防汛工地,几十人睡一个大通铺、吃食堂,“喔呀啊咧”又跟中学寄宿一样,有味!当躺倒在柴箩里(由两排成捆的芦苇摆成个“人”字形的简易工棚)的芦苇地铺上休息时,我和杨大塊不约而同地一弹而起,并连说:“不对!不对!根据各种迹象表明我们中了生产队设的调虎离山计了”如是两人一商量,还是决定立即返回二十几华里外的生产队去,这时,第一次出集体工的快感已荡然无存。
捱到满天星斗后,我和杨大塊才悄悄溜进家门,两位留守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她们今天安排在离家最远的地里干活,隐隐约约觉得队屋禾场上尽是担箩筐的人来来往往。我们的猜测更靠普了。快去把“高干子弟”润赖子叫过来问话(他爹是大队副业队长,故戏称为高干)。这家伙12岁的年纪才8-9岁的个头,只长心眼不涨个,放了学就在知青家玩,我听他姐姐喊“润赖子吃饭哒”这句话耳朵都快起茧哒。
我们按回家路上商量的办法实施,“润赖子你们家怎么比别人家谷分得多些呀?”我们以很随意又很知情的口吻对他说,他愣了一下,然后故作惊讶地反问一句“喔自个(当地语谁的意思)分哒谷”就这么四个对一个的套了他近半小时话都没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但根据他开始的那一愣,我们分析他家分了谷,已有人交代过这知青点的常客了,他不敢说而以。诈不行就用糖衣炮弹腐蚀他,我恭恭敬敬的递了根沅水牌烟过去,他接过烟斜叼在口里俨然一个大老爷们且一脸的春风得意相,我立刻划着火柴替他点着了。此招还行,受宠若惊的润赖子终于告知我们他家今天分到了500斤谷。看来他心里一直在做着思想斗争,只是不愿白白地当一回生产队的“叛逆”而已,如是,我们连夜去了会计家,看到账本上白纸黑字的写着-知青700斤,汤会计解释说:“此事如有人上告,队干部就都得坐牢啊,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所以才把你们派上工地去”。
那个年代,队上执行着所谓的合理密植,缺农药少肥料,亩产稻谷不足400斤,上缴任务为公粮80000斤,社员每年每户都仅分有够大半年的半饱口粮(这部分中还包括瞒产私分的那些谷),另外几个月放妇女儿童出去讨饭,而后就靠春插时国家下的返销粮来度日,当早稻收割前,队里迫不及待地组织社员下田剪还未熟透的谷子回家焙干解当务之急。就那么个现状,告密等于要他们的命啊!何况我们也指望得一份咧。但如果我们不从工地返回来,有不有份就很难确定了,因为,没有份的人,你就不会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这回事的人就可能是那没份人。帐外帐可随便写也可随便擦掉的,我们及时将自己列为了有一份的人大感欣慰。有一点可肯定,不论这次返队的结果如何,知青不会出卖润赖子,更不会出卖朝夕相处的农友。瞒产私分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和那个年代不可言传的公开秘密。
40年的事了,当年的那几位队干部都已去了那个再也不用担心温饱的地方,我却仍为他们过去为社员、自己、也包括知青所冒的风险而感动,并自荐代表7位知青向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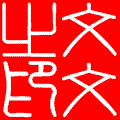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