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串联中的小故事
离农场不远是一座县中学,收工后或是农闲时,我们常到学校去看报打球。文革发动之初,学校里出现了诸如“毛泽东与王海容谈话”、“谭力夫血统论”之类的传单;8•18,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了全国城乡。随后北京红卫兵出现在学校,甚至还来到了我们农场。不要说那充满煽动力的演说,就凭那一口来自北京的、标准得令人羡慕的普通话,就足以让我们对被遣送到农场劳改的“牛鬼蛇神”——几个出身不好或是有历史问题的小学老师产生了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同仇敌忾,忘记了在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自己当“黑鬼”的经历,也忘记了自己的父母正在遭遇着同样的苦难。
山雨欲来之势使我们年轻而躁动的心感到了惶惑、惊奇和跃跃欲试。农场领导传达了上级的精神,叫我们不要因为天空中暂时出现乌云而迷失了政治方向,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毛主席对王海容讲过上课要打瞌睡,要敢于造反才有出息。终于,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个月黑人寐的深夜,背着领导和知青,我们徒步几十里,逃离农场,踏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征途。
把父母的担心抛到脑后,我们来到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地处现今芙蓉路立交桥的长沙火车站。车站一片革命气象,空气中弥漫着兴奋和豪情。在熙熙攘攘人群的裹挟下,我们挤上了一列不知道要开往哪个方向的火车,反正都一样——我们像水滴一样,融入了大串联的涛涛汪洋之中。
车厢被挤得鼓胀鼓胀的,过道上、厕所里,乃至行李架上都是人。没有列车员,没有广播,没有开水,更不可能有盒饭,列车走走停停,只有靠站的时候才能凭运气弄到一点水和食品。就这样,记不清摇晃了几天,在一个星斗满天的清冽的冬夜,我们神奇地抵达了本次列车的终点——北京永定门车站。
紧挨车站的先农坛体育场红卫兵接待站前,排起了不见首尾的长龙。还有数不清的人往一个方向蜂拥而去,问了问才知道那是进城的路。我们从接待站拿到了一个四位数的登记号,到窗口打探,才知道还在办理两位数的手续。我们不想在这里了无尽期地苦苦等待,于是加入了洪流般的人群,盲目地往城里涌去。我们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找谁,只知道北京有座天安门,是我们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在北京的容身之所。这时,天安门中间那个最大的门洞,成了我们心中的坐标原点,我们打算先到那里呆一晚再说。
夜深了,经过沿途大街小巷的吮吸分流,黑压压的人潮逐渐缩小成涓涓细流。这时,路也仿佛走到了尽头,一座古朴的城楼兀然矗立在前方,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走到跟前,灯光下分明显现出“正阳门”三个大字。面对这座庞然大物,立刻想起了“大前门”香烟盒上的箭楼,不同的是,眼前的正阳门已经实在得可以动用自己的全部感官去触摸、审视它的存在了。绕过正阳门,看到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产生了置身梦幻的感觉:深夜橙红的灯光下,一簇簇一串红散发出融融的暖意,天安门、大会堂、博物馆,这些记忆中的图像都历历在目,只是红墙青松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我的心底涌出了一股抑制不住的惊喜——我是真正到了北京,到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
走进天安门中间那个门洞,掩上西侧那半边满布黄色门钉的红漆大门,我们准备和衣挨过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忽然听到有人呼唤了一声:“还有谁没有安排好住宿?”仿佛变戏法一般,端门前广场上一下子聚拢来大群的散兵游勇。于是乎,一番向右看齐,报数,向左转,齐步走的口令之后,统统被收编到国务院接待站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阜成门内的华北局大楼。
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每个人都发了就餐证、乘车证。虽然是打地铺,却垫得很厚,暖气也开得足足的。解放军战士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我们是你们的勤务员,说着,把军大衣脱给了衣衫单薄的我们。随后把我们拉出去,在干涸的护城河河床上操练,准备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像个逃学的孩子,每天领着馒头、红肠,揣着乘车证和北京市地图,满世界胡乱转悠去了。
接见的那一天,早晨四点多钟起床,在昏黄的灯光下领好干粮,解放军战士领着队伍,忽走忽停,纵横穿插;马路上队伍交错,行止有序,俨然一派军事调动景象。天明时分,集结到西苑机场,列队等待。望不到边的人群中,漂荡出语录歌,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只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倩影。待到日薄西山,人困马乏时分,但见一溜车影急驰而来,旋即绝尘而去,顷刻之间,疲沓的红卫兵们连“万岁”也没来得及喊便一哄而散,各自东西,打道归营了。在夕照的逆光中,我依稀看到车上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想必那就是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至于林副统帅,仓促之中,暮霭苍茫里,也没有人去仔细辨认了。
回来以后,农场领导和知青们知道我们在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不免对我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仿佛我们脑后都升起了一个耀眼的光环。一位上级主管部门的书记谦恭地找我们打探时局,我们怀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马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露走资派的复辟阴谋。随后,我们也找主管部门批了一笔经费,拉起一面大旗,成立了红卫兵总部,虽然只有区区十几号人,远远够不上一方诸侯,割据军阀,袖标却做得尺许来长。在长沙城里招摇了几天,到底不知道坐标原点在哪里,也没有找到革命的大方向,终于土崩瓦解,悄无声息地作鸟兽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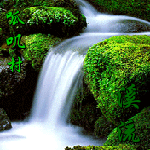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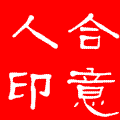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