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幼喜爱音乐,尤其痴迷于乐器。只因家境贫寒,无钱购买,故与大多数乐器无缘。上小学时,有同学吹竹笛玩,便好说歹说,终于可以与其共享,得以初涉器乐。中学时代很幸运地与饶世潢做隔壁班同学,饶是红领巾歌舞团的,后来以竹笛专长进了省团。每次课间休息听他吹奏笛子是极大的快乐和享受,并从中剽学了基本的技巧。班上同学有拉二胡的,我便也沾光学了一些皮毛。在9225宣传队我又学着拉京胡,还试图学小提琴,用的是速成法,记得最好的时候能勉强拉出《新疆之春》,但终因自己无琴而作罢。
小时候不喜欢上课,经常逃学。盖因三个地方吸引着我:电影院、书店和乐器店。我经常在五一广场东南角的那家乐器店流连,眼睛死死地久久地盯着玻璃柜里的各种乐器:镀银长笛190元、高级小提琴90元、红木铜轴可调弓带托二胡56元......看着这些标记着天价的乐器,心里充满绝望的痛苦。当我发现它或者她已经被人买去,更是愤愤不平,捶胸顿足。在电影院,每次都是溜进去的,看完一部后就躲进厕所,接着再看。电影让我暂时忘记了痛苦。书店特别是黄兴路古旧书店,那里面的长篇中外小说甚至民间传说几乎被我看了个遍。终于,我的痴迷让我做了一回孔乙己——65年在黄兴路新华书店我没交款把一本书带出了店门,被一个警惕性特高的女店员逮住。那是一本《二胡曲集》,标价2毛5分,里面有我极为喜欢的《赶集》。我被逮住的时候,脑袋里一片空白,然后是巨大的恐惧感。她很负责任地把我交给了班主任,一个平时视我如害群之马的偏执的女数学老师。
文革期间长沙街头经常有一个卖“土黑管”的胖胖的男人,每次发现他我都会凑过去看热闹。所谓“土黑管”完全是一种“山寨”版的乐器:用竹子代替了胶木,用塑料片代替了簧片,看起来极其可笑的玩意儿,但某些音色与黑管相近,大约5毛钱一只。其实在65 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卖的是“二胡速成法”,用数字代替指法,比如《东方红》第一句“SOSOLARE”换成数字就是“三三四零”,三代表无名指,四代表小指,零代表空弦。有时我还看见他在胡琴的琴杆上夹一支口琴,手口并用,同时演奏,眉飞色舞。而不论是他的“土黑管”、他的速成法还是他的演奏,其水平都是极差的,所以当时我是很鄙视他的。但现在想起来,我却对他产生了一丝说不清的敬意。或许是感动于他选择了用贩卖——即使是廉价地、低级地贩卖音乐这种方式来捱过他挣扎的人生。这个胖男人是我在文革中记忆较深的几个长沙街头人物之一,另几个是卖武艺的老人“丢丢丢”、百毒不侵的“槟榔宝”、过目不忘的“宣传宝”。
但是我不准备把“土黑管”列入伪乐器。我想说的是这样几种:一是所谓的“凤凰琴”。这种五十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好象已经绝迹了,似乎是被历史淘汰了。它的设计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按指和丝弦都是金属的,这就决定了它发出来的乐音无法避免地夹杂着难听的金属摩擦音。仅仅这一点就足够结束它的生命了。二是所谓的“秦琴”。它的问题是它也是作为普及品问世的,它实际是替代了“资产阶级玩意”吉他和不容易普及的三弦、阮等乐器,但又不具备它们的长处和特色,徒具形式而欠缺表现力。不幸的是,9225宣传队也有一把“秦琴”,它的爱主是甘棠塘头的洪江知青许家杰,外号“弹拨”。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把“秦琴”用它叮叮哐哐的声音并非和谐地加入了那个癫狂的大合奏。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葫芦丝”。我说它是伪乐器肯定很多人反对,因为它现在似乎已经进入大雅之堂,有改良品种,有独奏曲谱,甚至有考级!但不管它现在多么显赫,它也是个音色单调、音域狭窄的东西。我每次看见有人在吹奏它
时,心里就觉得厌恶,觉得吹者无素质,哈里哈气,什么乐器不好玩,要玩这种没觉悟的东西!
我现在呢,好多年都不玩乐器了。90年代初,花了8千多买回来一台珠江牌钢琴,至今没有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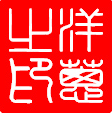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