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读书无用”的年代当老师
1972年我转点到汨罗县,在大队教了一年小学,又被调到公社中学教初中英语。我原来只学过俄语,虽然再三声明,公社领导说反正差不多,边教边学吧。就这样,我又干上了下乡之后的几乎第三十七行。
教了两个星期,还真像他们说的,确实有些“差不多”。
头几天,发觉有几位老师总是在与我上课的教室一墙之隔的教师宿舍里一呆一节课,我想他们是在考察我这英语老师是不是一位“南郭先生”,于是我扬长避短,尽量避免朗读和课堂用语,大讲词法和语法。俄语是一种十分年轻的语言,语法较之英语复杂得多,有俄语垫底,讲英语语法就是小菜一碟了。而英语和俄语单词在词义上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一个family我可以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地讲上一、二十分钟,只是读起来像俄语的发音:发米利亚,不过这一点也许是那隔墙偷听的老师不清白的,不然他们就可以自己上台了。后来他们不来了,也许是折服于我的“渊博”了,我想。
另外,我敢抓课堂秩序,这一点也让校长对我刮目相看。
当时河南发生了所谓的“马振湖公社中学”事件:一个女孩子自尽了,被上纲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对贫下中农子弟的迫害,该校的校长被抓了起来,还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我们校长从县里回来非常反感,非常抵触,在全校教师会上声明不予传达。老师们对事件的报道尽管心存腹诽,却更须明哲保身,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学生的违纪不闻不问,免得“激化矛盾”,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学生最头疼、最不愿意上的就是英语课,为了维护课堂秩序,我把搅乱课堂秩序的学生从教室里拖了出去,校长对此保持了沉默。
这一期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兼了一门历史课。
自文革复课之后,《历史》一直停开,这期开学后忽然通知加开,使用的是北京市新编的教材,学校把这门课交给了我。我参考手头仅有的一本吕振羽著《中国通史》,从类人猿、类猿人讲到北京的山顶洞人,从夏商周讲到屈原行吟泽畔,自沉汨罗。
历史课真好上,孩子们全神贯注,若有所思,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奇和赞叹。课后,学生们,包括英语课上被我赶出教室的学生围住我问:“老师,屈原投的就是我们这条汨罗江吗?”当他们从我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才不胜唏嘘,议论纷纷地散开了。那时,劳动和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冲击教学是很平常的事,随时可以“因故停课”。被“读书无用”麻木了的师生对停课也很无所谓,唯独缺了历史课,学生们会围着校长吵着闹着要求补课。
过了几周,大约还没有到得了汉朝,学校又接到通知:历史课停开。学生们找校长显然已经无济于事,又不可能上县里、省里,更不用说到北京去请愿。历史课终于停开了,我没有像韩麦尔先生一样把最后一课上得十分悲壮,只把《中国通史》又埋进了箱底,还有那本历史教材作为陪葬。
孩子们喜欢历史,尤其当他们从历史中感到一种贴近,一种厚重,因而引发他们的思索,因而使他们走出幼稚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了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对世界的认同。
历史证明,割断历史是愚蠢的,历史也是不可能被人为地割断的。












 刷新即可分段了。
刷新即可分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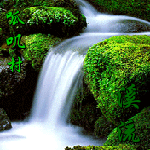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