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片浮云拥着如银的月亮,从垄那边的野鸭岭上缓缓移过来,照着我们曾经辉煌过的艾山冲山 庄,早已门庭冷落的旧宅前面便寂寂地泄一片苍白。我和母亲、还有三伯母坐在地坪里歇南风,禾田里暑气刚刚散尽,偶尔听到草叶摩挲发出的细碎响声,母亲手中轻轻摇一柄蒲扇,眼睛却出神地望着那一轮欲露还藏的月盘儿,好久好久不吱一声。我依稀记得三伯母说了句“菩萨会保佑他平平安安的······”母亲才迟疑地将目光落在我身上,三伯母吃花斎,家堂上供一尊观音坐莲铜像,无论何时,手里总是拿一个柄端上吊着玉坠儿的拂尘。长辈们说的话,我们小孩子家是听不懂的。月儿将大半个脸儿隐在云层里,一忽儿,又从另一片云絮中悄然拱出来,迟归的鸦雀几声啁啾,辽远的夜色里立时静如止水。我枕在母亲的膝头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如水的月辉淡淡地洒在古城一条细细瘦瘦的麻石小巷里,小巷两边红砖青瓦、屋舍俨然,巷民们有布庄的老板,写戏的先生,也不乏皮匠。裁缝和拖板车的苦力码子。满身乡气的我怯怯地站在一根木电杆下,顶上带瓷盖的路灯昏暗如同虚设,巷子里各家老小围成一个圈儿,抽烟、喝茶、讲古,或生意上的起宕、或戏文里的曲折,直侃得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大男细女笑语连连,那种热烈、那份温馨,在一个乡下孩子的眼里是極动人的。忽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喊了我一声,猛一抬头,泪水便扑簌簌滚落在母亲的衣襟上,母亲轻轻给我拭去泪水,又帮我将七上八下的衣服扣子重新扣好,牵着我的手向巷口走去。巷口上,刚刚落成的银行大厦一侧有道矮围栏,我们在上面坐下来,月色凄迷, 街灯昏然,周边行人稀少,偶尔一辆背着炭篓的公共汽车老牛破车似的从面前驶过,隐隐绰绰的月光下便拖一鞭黑云。我忽然痴痴地重复着一句问了不知多少回的话:“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好半天,母亲才侧身抚着我的头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些年了,信也没回一封,还不知······”声音便有些哽咽。那一年我刚刚七岁,孤儿寡母的,在乡下难以为生,母亲便到城里与人帮佣,将我寄住在姨妈家,母子相聚的时候不多,可在一起时话也很少。月色淺白,像是一位分娩不久的少妇,慵懒且无可奈何地照着巷口上相依为命的母子俩······
八月幽风里,一轮明月冷清地挂在村口大樟树的梢尖上,将屋舍、池塘和远远近近的山峦田垄照得白晃晃的。这是南方都庞岭下的一个小村,命运注定我和这个村子结下了缘分,二十岁那年,我吸旱烟的水平 已经相当不错,白日里上山割草挖荒,晚上坐在破祠堂里开会学毛选,腰里常兜着个烟荷包。中秋之夜,我和村里的单身汉贵满伢子学城里人的派头,坐在河边的小木桥上吃饼甞月,贵满伢子脾气丑,常和人吵架,对我们却很照顾,落雨的日子,
常来我们知青屋坐一会。此刻,我们 嚼着那坚硬如铁的饼子,眼睛便随着纤云托起的月盘儿移来移去“莫非月亮也是无情物?一会儿挂东,一会儿移西的。”贵满伢子咽下一口饼子自言自语说。我没吱声,心里却想,月盘儿载着那么多人沉重的心思,村口那老樟树的梢尖尖又如何承托得起呢?难怪她总要走的······
月亮移在滴水岩如墨的峰顶时,我已是一个挖了三年多水库的老民工了。这是一座中型水库,各队都来了好些能够挑土打夯的后生子,寒气逼人的夜晚,我们穿着草鞋在大垻基坑里刨石头,月冷风清,腹中饥饿,我和队里的小狗偷偷溜回工棚烤火,抱膝坐在只有余烬的树蔸火堆旁,不知不觉竟睡着了。一阵急风将河洲上的芦苇吹得呜呜作响,猛然惊觉,慌忙钻出工棚,循着惨兮兮的月色,逃也似的赶往工地,刚刚从地上拾起锄头,凄厉的哨声骤然响起,于是,一场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小狗比我聪明,弯腰凹肚作无限痛苦状,赢得了许多人的怜悯,我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勾着头呆呆地立在人圏里接受革命群众的唾骂。半个月亮从云隙里爬出来,我想,素常洁白无瑕的月儿见了我这副宭相一定很为我害羞······
岁月如流,世事迁变不迭。壬申年桂子飘香时节,月盘儿终于越过重重关隘,渡过滔滔南海,将它那充满温馨柔情的清辉播洒在椰叶飘摇的台湾岛。我和睽违了四十载的父亲坐在盆花溢香的小院里感受月光,四十年椰风蕉雨,染白了父亲头上的青丝,却没能改变他那一口浓重的乡音,家乡新事,骨肉亲情,说不尽,道不完,妹妹送上来果脯和烤肉,父亲只淡淡地瞥了一眼,说;来点儿酒!是啊,此时此境,倘没有酒,岂不是辜负了这美好的月色么?
风轻,月圆、酒香,父亲和 我都陶醉在这如梦的境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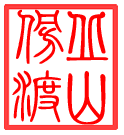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