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涩的少年时代(续四)
回到长沙家中,报上户口和粮食关系,才知道我每月只有27斤口粮,这对我一个吃了一年多45斤口粮的人一下子去掉了近一半,今后的日子难熬啊。
家中父母的生活费是大姐按月20元寄的,一下子多出一个人也不能要大姐再多寄点呀,因为她的工资也不高啊,只有出去找点活干了,找了近三个月,各单位都己“精简机构”了,哪会有事没人干呢?一直以边帮父亲糊水泥纸袋边找活干的,这下泄气而绝望了。
天无绝人之路,区政府号召義务修“黄花渠道”管吃住不发工资,定量粮食35斤,二话不说报名了,这种工作我还能吃得消,不就是挖土填土吗,早在初中时学校组织修“京广复线”就锻炼过的了,每天嘻嘻哈哈的倒也容易过,下午收工后吃过晚饭洗洗脸脚就都爬到地上舖层稻草的大统舖上去了;呑云吐雾、天南海北、故事神话、胡吹乱说,夜里十一点过后,人们都渐渐地睡着了,我的心事又涌上心头:今后怎么办?天天晚上想也没找到答案。
偏偏又是春节前,工地完工回到家里,我又过了一个郁闷的春节。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就要满十八岁,正是这个时候,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大姐要生孩子了,让我母亲去伴月,下半年动身,第二件事是东区有一所民办机械中专学校下半年招生,我的事情多了,白天想方设法赚钱,后来终于进入了一个土方队挑土,并商定好做到开学,晚上把过去的书找出来开始了复习。
母亲是七月份到北京去的,我是九月初开学,大姐当时说明了母亲走了以后仍按月寄回来20元做生活费,学费自理,好在学费不算高,我上半年的收入够读一年的了。
虽然是民办学校,但师质力量还是够强的,除校长外,这些老师大多是一九五七年下来的大学老师,讲课生动,同学们易懂好记,转眼读过了一年,我沉浸于知识的海洋里不能自拔,但现实摆在我面前;九三年下半年的学费哪里去赚?
不知什么时候起,街道上做起了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他(她)们说话又不要负责,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塘里有鱼屋前有花”……不一而足。我好不容易在一家锻造工厂找到一份拖煤渣的事做,只要运出厂,不管你倒到哪里,每天上下午各一车(板车),运了一、二十车,会计叫我去结帐,我心想还不够学费不暂时不结,可是会计不肯就要当时结,我一点也不会想到这里面还有文章。结帐时要我去办事处开发票,来到办事处,说我是上山下乡对象,不肯开发票,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同意开己经做过的票,并喊应我再莫做了,否则不开票拿不到钱莫怪人。
书还是要读没钱可不行,民办学校老师的工资在这里呢!忽一日报纸上看到一篇市立一医院要求献血的通知,心中一动,偷了家里的户口薄,瞒着父亲去报了名,事情还算顺利,第三天来了通知去体检,被邻居一位老人家接到,晚上三位老人把我叫去给我做工作,不同意我卖血,我向老人们哭诉着我的无奈,她们才极不情愿的将通知给了我。
抽血300毫升,给了42元钱,还有半斤油票、两斤肉票、一斤糖票。心里松了一口气,总算又可以读书了。
天有不测之风云,街道上的人经常上门,照理说我一个在读学生怎么就成了下乡对象了呢?跟我说不通就找到父亲头上,他老是不敢不同意的就推到母亲头上,写信到北京,大姐来信也是做工作,还有什么你也十九岁了,总不能要我养着了……。这时候母亲还在北京也无法说服大姐。当时下乡地一是江永的农场一是长沙县路口峹(音沙)公社,而在那些人嘴里江永好多了,我也不完全是求好,也想远离这是非之地,选择了江永县铜山岭农场。
离开长沙那天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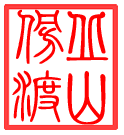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