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乡下几年,我最怕的农活就是扛木头或者担牛粪,因为我力气小,这两样农活强度大,而且不会因为你的力气、年龄或身份如何有任何照顾,完全按抽签的次序排到哪一段你就得在哪一段干活,也正因为这个活路是接力进行的,连休息的机会也没有,再累也得咬着牙干到底。但是我又很愿意干这种活,因为工分高。
扛木头除了用力以外,还得有点技巧,尤其是步伐一定要和同伴保持一致,否则不但费力,而且还会有危险。其中一个原则,木头在肩上,无论如何都不能随便扔,否则就会伤害到其他人,甚至伤害到自己。在一些特殊的路段,同伴间的配合更是重要,互相之间一定要协调,还要互相完全信任。有一次,我们扛木头出冲去,过贺家附近的一座木桥,几根木头靠不到一起,两个人还得并排过桥。这样,我们只好采取过独木桥的办法,两双脚意义的踏在同一根木头上,两人各自使劲往两边倒,身子全部悬在桥外的上空,形成一个到三角的形状,一步一步移过桥去。这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害怕了,不敢悬在桥外,稍微松一点劲,那么两个人必定全掉到桥下去了。
危险的事还是发生了。那是72年初在大队修水库的时候,经过一个冬天水库大坝已经成形,这一天要一批人到山上抬木头,大概是做闸门用。这是一批前两天刚刚砍下来的生木头,每一根都非常重。我和风子合作,负责一段下坡。当扛到一根特大的木头时,出事了。
我们扛着这根300来斤的木头下一道长墈,墈很陡,肩上的木头都已经成了45度,重量基本上压在前面我的肩上。突然,风子脚下的一块石头被踩脱了,一个趔趄,整根木头向前一冲,我几乎被着冲力推倒了。这时,只听到“啪”的一声,我的背上一阵剧痛,不好,闪着腰了。一下子,豆大的汗往下直流。过去看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豆大的汗往下直流”的说法,这一次是自己亲身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汗并不是从皮肤表面渗出来的,而是浑身的毛孔张得大大的,就像打开了一个个水龙头,汗水直接从这些龙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汗水也不像平时那样顺着身子往下淌,而是直接喷涌出来,掉到周边的地上。我感到全身发抖,剧痛的感觉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半秒钟也坚持不住了。但是,我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持,一旦我把木头扔下来,我在下方木头在上方,而且木头在我的内侧,即使我把木头扔出了我的肩头,仍然会从我身上滚过,几百斤的大木头之下,我绝没活命的可能。再说,风子在上面,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也很可能被落地后弹起来的木头砸伤。我只好硬挺着,一步一步走下这道长墈。等到了下面的田里,用“师傅”把木头支撑好,不敢再往前走了。这个地方还不到我们预定交界的位置,风子大声喊叫要后面的人过来接过木头。
木头终于被人接过去了,我一松劲,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如今,只要天气不好,我的背部就会疼痛。又因为受伤部位骨质增生,我的脊椎一直是弯的,当兵的时候,为了把身子挺直,我不得不使劲往右边别住身子,否则身子一定是往左边偏的。这都是那一次扛木头给我留下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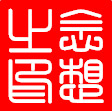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