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斗会“流产”记
1969年1月15日正是戊申年三九时节,我随省城望麓园街区400名社会知青和成户居民下放到了桃源县茶奄铺区杨溪桥公社(随后的2月中旬街区又下放了300人到茶奄铺公社)——那是一个令我们所有下放人员永远无法忘怀的摧心日子,那是一个叫我们毕生刻骨铭心的悲伤日子,那是一个使我们一回首一想起一提到就会哭泣的蒙难日子啊……
在白雪皑皑、寒风呼呼的冰天雪地里,我们这数百个都市的下放人员就像随风飘零的雪花一样,被无情地抛落在湘西北那片偏僻山冲旮旯里。从此伴随我们而来的是那漫无边际的遥远等待;可等待而来的却是希望幻灭之后的失望打击,乃至到最后剩下的就是厄运留给我们的绝望挣扎与饮泪呻吟……我们的青春岁月从此就与幽深的牯牛山峰黎明相伴;我们的人生之旅从此就与荒僻闭塞的杨溪乡野黄昏结缘;我们青涩的初恋、花季的梦想和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憧憬都随着残月冷风飘走,永远地失去了……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这批下放人员中不少是成户居民,他们在乡下遭受的磨难比我们单个下放的知青更大更多更惨!其中一些家中的人客死他乡——至今都是漂泊的孤魂野鬼:有在雪天里被赶出屋、抛掷在牛栏里门板上而慢慢冻死的街邻修鞋老头(我和大个子路过时亲眼见到他僵硬的尸体);也有因双抢得急病而累死的清纯花季少女(我父亲“同事”的次女);还有下放后伴着一盏残灯患牙病打错针致死的可怜孤老婆婆……那些冤屈的阴魂已经像梦魇一样紧紧笼罩着我们的心窗,驱之不去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成为我们苦难人生旅程中的青春驿站,它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用生命血汗浇铸的心碑上,岁月的沧桑抹不去!时空的利剑砍不掉呀!
为慰藉自己这颗日夜不安的悸动心灵,为告慰那些将生命捐献在第二故乡的昔日伙伴,为垂怜那些因丢失了青春灵魂至今仍居无定所的知青流浪者,现将桃源往事中我们大队批斗憨弟的事件记述如下,聊作纪念!
(一)
我们向阳大队共下放了三十名知青,男女各一半,因我们是街区下放,完全没有像学校下放那样考虑“男女搭配”,只有少量原来很熟的街坊玩伴组合下在一起。我下放的干溪队共落户三人,另两人为大个子和憨弟。大个子是我在下放前约好的,憨弟是在公社分队时加入的。大个子住在我家隔壁,他本已将户口迁往同学们下放的岳阳,我送大妹落户沅江返长后仍躲不脱下放的厄运,就叫大个子将户口迁回街区与我一起走。憨弟住在我家斜对面的巷里,他兄因“猪婆风”留城,于是就叫十六岁的憨弟替兄走,在公社分配落户队时,我见他一人打“单吊”,就要大个子同意他与我们下到一队了。
我们三人那晚跟着赫队长和另一社员到了队,即受到聚在毛木匠家队干部和社员的欢迎。我们公社共十来个大队,我们大队不到千人,处于一个较长的狭谷中,从西至东有二、三里长,南北窄了一半,均是不太高的山岭。西边的山脉高些,但有一条崎岖的小径通往区镇茶奄铺。唯有东边是一个“口袋”形的大缺口,每天早晨太阳就是从那个方向射进狭谷里的,大队之名也由此而来。缺口的这边就是从我们左邻弯溪队后牯牛深山里发源流出的清幽杨溪河,这河在缺口的地段转了一个急弯,再朝着我们公社所在的马路方向奔淌而去,最后汇入沅水……比起其它大队来,我们向阳大队在公社中还是一个地域不错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地理位置竟然是其后发生罕见的龙卷风的灾难之地。
我们三人落户干溪后,住在毛木匠家的一栋双层旧楼房里,楼上住人,楼下做厨房,新的日子在沉闷中开始了。令我们非常失望的是:大队的十个生产队中,干溪队竟然是最差的队。队之差首先从队上的人户反映出来,五十来口的小队单身男人就有七人,加上我们三个,正好一个“大满贯”。其次是队上的田土位置偏高,因而造成要水的时节没水,不要水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受山水袭击。再者水田的土质也没有下方队的土质肥,旱土也多散落在高耸的南边山岭中。
(二)
虽说憨弟是一个五尺男儿,但他天生就有点“憨”,也不知是不是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饿出来的不?那时居民在街区吃“集体食堂”。我记得每次开饭时,他总是去抢他哥哥钵里本就不多的二两烂巴饭,他哥哥不发病时有时也用筷子挑一小坨给他。于是,吃不饱的憨弟就去挖旁边弟妹们碗里的饭,由此自然闹出乱子,经常是他碗里的饭没增加,倒被别的大孩子挑走了,最后他就坐在我对面的“三三食堂”门槛上哭叫……他的父亲也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躺在床上,那还顾得上管儿女呢!憨弟长大后人确实有些“呆滞”,街坊都说他老实。
有人褒奖说:老实人做扎实事!也有人讽刺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后一句更有它的道理,憨弟刚下放就闹出不少笑话啦。第一次夜晚去屙屎,他就将脚踏进了那个“金字塔”似的小口的高粪木桶里抽不出,弄得一身臭气熏天,骇得我从楼上跑到楼下的茅屋里……开春后我辛辛苦苦种的白菜秧苗被他“拔苗助长”后,几乎全部枯萎夭折,弄得我对栽菜顿时失去了信心。每人轮着做早饭,憨弟第一次就将白米煮成“黑饭”,使得大个子和他吵了一架,我从中做调解,仍然不欢而散。没多久憨弟提出他一人开伙,因他与大个子总为一些家务琐事吵嚷,夹在中间要作”和事佬”的我无奈同意了。我与大个子虽有些生活习惯的差异,但我想到他离开同学而跟我来桃源的这份情意,自然就相安无事了,于是,憨弟就单独开伙了。
憨弟另立门户后,“毛病”越来越多,笑话也接连不断。先是将猫打死在箩筐里,将猫肉和着猪肉一起煮着当杂烩吃。接着又忘情地投入追右邻茅溪队的栀妹中,栀妹可是当地一个长得非常水灵的少女,身段好,肤色秀,五官红润,人儿娇嫩,简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笑!古人是“月下追韩信”;他却是“月下追乡妹”。虽说最终他没追到手,但毕竟也在我们茅溪队放电影时与栀妹唠叨了几句“情话”。其后队上的香嫂倒是被他沾了腥,绯闻一下传遍了整个大队……笑话倒不要紧,它不会伤身,问题就出在他的毛病了。他咯个人因年纪小不会照料自己,搬到东头毛木匠二哥毛篾匠家(毛木匠三兄弟的房子连成一栋很长的两层木板房)后,比与我们在一起时更不讲究起居卫生了。房里自然是一团糟,个人卫生更不要讲了,只有傍晚去幽会时才会临时将衣衫整理一下,将头发抹一下。他家里的条件甚至于比我还差,偶尔搭一点食物来,他一两顿就全部吃完。中午从田间干完活回来,一发懒筋就吃一碗冷饭,没米时就只嚼一把苞谷(我们那里中餐是喝擂茶加苞谷)。时间一久自然得了胃病,但他折腾得最大的一次却是那次开春后淋湿全身后发烧不止、全身直颤,最后弄到公社卫生院住了好几天的那场大病。
(三)
憨弟那场大病首先是从清明下种后的秧田淋雨后开始的,他起初也只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他仗着年轻也没有在意。直到几餐有饭都不想吃的时候,一连两日未出工,毛篾匠叫我喊来赤脚医生给他开了两服草药,但他喝了毛嫂子煨的草药并不见效。到第三天上午巳时,我发现他烧得很厉害,没了主见,喊大个子过去一看,只见他躺在那张平头单人床上,盖了厚被子还全身直抖。大个子又将壁上挂的蓑衣盖在他被上,还是不行,他说:“只怕是虐疾呢!”
我说:“怎么办?”
毛嫂子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她丈夫出外做篾匠去了。大家都没了主见,毛木匠闻讯进屋说:“还呆滞什么?快将人抬到杨溪桥卫生院去。”
我和大个子觉得这是唯一有效的措施,拿什么抬呢?那时又没有轿子,抬人在弯弯曲曲的山径上行走多么吃力呀!还是毛木匠脑袋快,他说可以用有盖的猪笼子抬。这种两用长方形猪笼有一米多长,一面档头有门,顶上也是活动盖。我和大个子异口同声问:“谁家有这种猪笼?”
凑巧的是这种猪笼干溪队没有,只有到弯溪队去借。事不宜迟,大个子起跑到弯溪队借来了这种平常赶猪送猪的长木猪笼。正巧缺口处向阳生产队矮小的男知青“小粒子”来了,也加入了送憨弟的行列。
大个子和毛木匠赶快将憨弟从床位上抬下,准备让他“进笼”。毛木匠叫我将猪笼上方的盖掀开,放置一张矮木折椅到笼中,然后小粒子从床上取下一床棉被垫在椅子上。我暗暗叫苦:“老弟就屈就一下吧!”
随后,我们几人七手八脚将憨弟塞进了猪笼,准备上路。我的体力不行,要抬六、七里是吃不消的。大个子看出我的担心,说:“到对面溪桥后我们再喊眯哥一起去。”我点了点头。
我在前,大个子在后,各将笼上的两根竹杆搭在肩膀上,终于抬着猪笼中的憨弟上路了。抬到溪桥前我已满头大汗,赶忙歇了下来,叫小粒子先过桥去喊眯哥来接肩。我们刚过五十来米的溪桥眯哥就迎了上来,虽说平常都显得有些懒散,但一遇到知青中有什么事,相互之间倒是行动满快的,从不讲什么条件。
过桥后眯哥就是抬猪笼的主力了,他生得一米七余,身板尚结实。小粒子也太嫩稚了,只试了一下就说抬不起脚,他基本上没有抬几步。过桥后我在过溪岭后接了一肩,此后就是眯哥和大个子抬的。到卫生院一检查,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否则憨弟就危险了!憨弟在公社卫生院住了个把星期,住院费是在知青费用中报销的。出院时他瘦了一身肉,因他得的是急性肺炎,系由感冒发烧引起,但对于多灾多难的憨弟来说,这一切还只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呢!
(四)
憨弟从医院回到队上后,休息了几天就回城去住了半个月,但他家境确实太困难,一家五口人主要全靠父亲微薄工资度日,他母亲的街道小厂收入更少。而他患猪婆风的哥哥也要靠父母养,一个妹妹又小。本想养病的憨弟又回到了干溪队,他得病后出工就大大减少了。
时光一晃飞快地到了要双抢的时节,这是一年中最累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抓得非常紧。这个时期内憨弟出工比我和大个子都少多了,实际上这与他的身体在春天得的那场大病有关。说到就到,阴历六月带着它火辣辣的阳光降临了,每天没有亮都被赫队长喊醒下田去扯秧。我快要吃不消了,也只好硬着头皮起早贪黑做,总之,尽量避免那些实在奈何不了的农事,譬如下田挑湿谷就是我最害怕的活(只有插秧我不怕,我的手脚在队上属于前五名,曾被派往深山的牯牛公社换工)。憨弟在这繁重的体力活前无法承受,刚准备打退堂鼓,就遇到了一次最严重的打击——他被大队民兵抓到大队部开大会斗争。
事件起因是由双抢引起的,但赫队长早已对憨弟有意见:成见源出他每次去喊憨弟做早请示都被挡在门外,憨弟是队上唯一不去队屋早请示的人。然而真正促成这件事的却是干溪政治队长冷黑子,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瘦汉,做事阴毒,擅长背后整人。他对几个知青都不友好,终于趁双抢机会抓住了憨弟的辫子。
这天中午杏花生产队的冯兵来到憨弟住处,告诉他没米下锅了,准备明天回家。憨弟也诉苦:“赫队长扣住我的指标粮不发呢!”
冯兵趁机动员他:“我们一路走算哒!”
憨弟点头同意了,并约好第二天清早在杏花村队口碰面出发。傍晚起憨弟就开始做准备,收拾行李。不料他的这一举动被住在他屋后不远的赫队长发现,赫队长晚上碰到黑子又告诉了他。黑子随后到茅溪队找到大队民兵营长告了密。章营长人称章猴,这瘦鬼是靠在公社的一个亲戚拍马屁上去的,对待外地移入之人素来排斥,知青没来前他对湘西迁入的土族人也常刁难,乡民都讨厌他。
第二天,蒙蒙亮憨弟就动身往杏花村口去,刚走过茅溪的大坪,突然间蹿出来一高一矮两个民兵将他捉住,随后猴子营长与民兵一起把憨弟带往设在油坊的大队部。向阳的大队部设在油坊已多年了,因油坊位于整个大队中心,在油坊的北边是大礼堂,礼堂能容纳数几百人,大队所有大会都是在里面开的。这天大队本有一个斗四类分子的例会,猴子营长临时决定将憨弟一起斗。这闭塞的山谷里文革前大会不多,自从文革闹起后,人们似乎也习惯了“三日一小斗、七日一大斗”的场面,只是苦了那些挨斗人员,每次开会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将知青与四类分子一起斗争,这还是头一次,许多社员不理解,都站在一起讥讥喳喳。这时冯兵得讯民兵抓走憨弟,马上通知其他知青都去油坊集合,准备与斗憨弟的民兵正面交锋。猴子营长此刻也与大队梅副书记来到了台上,各队的社员已经来了不少人,一场剑拔弩张的斗争会眼看就要开始了。
原来斗茅溪地主分子弯背老倌的大会变成以斗知青为主的大会了。又矮又胖的梅书记最逗知青讨厌,特别是他见到女知青时流口水的那副哈巴相令人作呕,无奈的是又都不得不对他笑脸相迎。他见太阳老高了,这时站到台前宣布斗争会开始。连怎样抓双抢也没有讲,就要猴子营长宣布憨弟的“三条罪状”:一是对抗早请示;二是骂队领导;三是逃避双抢。
猴子营长刚宣布完憨弟的所谓罪状,就举拳喊“将逃避双抢的坏分子押上来!”两个粗壮民兵将捆了的憨弟押到了台中央前方,憨弟虽被推到台前站着,但他并没有胆怯之相,头也没有低下,只是满脸露出忿气,不屑一顾的样子。台下前方此刻已挤满了向阳大队的男知青,站在最前方的是眯哥、冯兵、高军、冬瓜弟、大个子、小粒子等人,女知青有霓姐、雅俐、秀妹等人……我移到台侧右边观察,心脏“咚咚”直跳,知道一场大架就要开始了。
猴子营长的音未落,眯哥突然带着我们喊起来:“不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不准打击知青同学!”……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显得特别严重,一些社员也开始哇喊哇叫起来……喧哗的叫声和骂声此起彼伏,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就像一锅煮开了的水沸腾了!危难时期显身手!正当高个民兵将憨弟的头强压着往下按时,好样的眯哥一跃而上,飞到了一米多的台上,将高个民兵往后一推。随后在公社知青中享有“摔跤王”之称的高军也站到了憨弟身边,矮个民兵见魁梧的高军近了身,忙往后退。他领教过高军的功夫,曾在杏花村与高军“摔苞谷”,那是刚下放时的事:队上十几个青春年少的伙子一个个排队与高军较量,一个个被他摔得鼻青脸肿,几天都躲着羞见旁人呢!高军和冯兵读初中时曾与校内号称星城“十三太保”之一的桶胖子练过拳脚功夫,果然到乡下还显了一回威风,今天关键时刻又派上了用场。
说时迟,那时快。眯哥欲扯着憨弟跳下台溜走。猴子营长亲自带着三、四个民兵又围了上来,他指挥两个民兵先将眯哥捆绑住再说,有一个民兵用木棒在他头上重击了一下……高军此刻正与高个民兵交手,冯兵则与另一个民兵扭成一堆,台上撕扯打成一团。台下的社员们已经往台前挤过来,我看见被挤的女知青在喊叫。如果乡民的野性被挑唆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况且人数少得多的知青们最终肯定要吃大亏的!正在这时,一个女知青跑来大声叫:“不要打了,桂书记马上到!”
人们一看,这个大叫的原来是雅俐。她的声音一落,打斗的双方慢慢停下来。桂书记在社员和知青中都有威信,他这人比较正直,对知青也相当照顾,所以讲话别人服从,也只有他来才能制止得住这场斗殴,这时他已经骑着自行车从公社赶回来了。
桂书记向梅副支记简单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没容站在一旁的猴子营长插嘴就大声斥责道:“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怎能这样对待知青呢?”
接着他对围拢在台上的知青和台下的社员们说:“今天的大会就不开了,大家快回家,这件事我下午即去公社汇报,一定要严肃处理。”
一场来势汹汹的斗争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原来准备挨一场皮肉之苦的弯背老倌也侥幸逃脱了惩罚。知青们于是一个吆喝,都往杏花村队去“庆祝”胜利了!在那里听眯哥给我们吟唱了他刚创作的《月光照耀着杨溪河畔》的歌曲。
后 记
在向阳大队知青们全部返城后的某一个夏天,同是在向阳大队油坊大礼堂里,同是在六月双抢前的一个炎夏午时,同是全大队数百人站在礼堂里开大会的一个时刻——一场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罕见“龙卷风”风暴突然袭击了这个长狭谷,仅仅几分钟时间内,风驰电掣的冰块雹灾就使整个油坊大礼堂的木板建筑,在“轰隆、轰隆、轰隆”的巨响声中一下全部坍塌了……最令人难解的是:当冰雹袭击前刮风时,绝大部分人已经撤出会场,各自散开躲避,而在台上的猴子营长、冷黑子首当其冲被第一根倒塌的横梁同时压死。梅副支书是最早从会场逃出的,他本已经脱离险境,却在过溪桥时,被突然尾随追来的一阵狂风将横跨溪河两岸的木桥桥墩连根拔起,将他摔到半空中,然后再扔进泥田中,结果他的臀部遭受重伤,股骨断裂,只能坐在轮椅上苟延残喘,惨度余生了(此龙卷风灾难曾见诸当时报端)。
最使人难过的是眯哥在那场搏斗中头部遭受暗伤,导致他后来神经中枢失常,回城后又失去工作单位,父母辞世后他就在省城的芙蓉路上以流浪为生,每天早晨从北端的伍家岭出发,一直沿着马路往南走,走到涂家冲尾段再回头重新往北走……去年底,下岗的大个子还在寒流袭击时给每晚睡在立交桥下的眯哥送去了一件大棉衣。
憨弟的结局已经在《憨弟二、三事》一文中作了交待,不再赘述。
(写于己丑年二月初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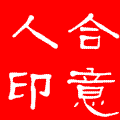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