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间平常事(3)——桥头那个算命人
去年我回安乡,大春告诉我,安乡大桥靠安乡那头的桥头上,常常坐着两个女算命人,其中有一个是福伢子,另一个是她师傅。
1969年1月6日,师院附中近200名青年学生乘船来到从未听说过的安乡农村插队落户。我与M来到一户农家。这家有三代六口人:爷爷,奶奶,父母,一儿一女。后来才知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已成婚,另立家室了,二儿子去年参军了,身边小儿子读三年级,唯一的女儿排行老三,14岁,小时候得病,病愈后不幸成了瞎子,小名叫福伢子(乡里的习俗是把男孩叫某妹子,而把女孩叫某伢子,说是这样好带些)。直到今天,我也只知道她叫福伢子。
在这落户的日子里,福伢子渐渐与我们熟起来。收工后,我们帮户主家挽草把子,她就帮着摇把手;我们帮着添柴煮饭,她就坐在你身边跟你聊天,问这问那;我们帮着拣菜,她就摸着帮你递菜;我俩聊天,她也在一旁仔细听,不时问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比如:“红颜色是什么呀?”“姐姐,你们是什么样子啊?我好想晓得的。”
我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盲人,更没有跟他们说过话,没想到在这里天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人跟着我们。我深深体会到这是多么悲哀:她还小,现在跟着父母过,事事有人照料,长大了怎么办?眼睛还能重见光明吗?我问过她妈,她摇着头,叹着气:“唉,没希望啦!”有一天吃过中饭,我坐在门前禾场里晒太阳,福伢子也紧挨着我坐下,开始了天真地问这问那。我耐心地一一作答。我发现她面带笑容,“哦,哦”地应答着,但是,老皱着眉头。我就问她:“你禾解总皱着眉头咯?”
“什么是皱着眉头啊?”
“。。。。。。”
我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要她用手去摸自己的眉头,边说:“这就叫眉头,边上的肉是果样子就叫皱着眉头。”她反复做了几次,还开心地笑起来:“果样子就叫皱着眉头啊!”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后来,我们搬进知青屋,她还常来找我们玩。毕竟不方便,慢慢联系就少了。再后来,知青散了,我也到大队学校教书去了,几乎很少见到福伢子了。
有一年双抢时节,队里来了一位“扮禾佬”。所谓“扮禾佬”,就是到外乡帮助扮禾的男劳力。他个子有一米七三左右,瘦瘦的,人还老实,做事还里手,大家评价还不错。这一下不打紧,有风声说给福伢子对上了相。不久,结了婚,生了个儿子。
我很久没看到她了。听说她就住在堤边的某一幢房子里,有一天特意抽空,我去看她,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家。来到禾场里,我就扯开喉咙叫起来:“福伢子诶,福伢子啊,在屋里冒咯?”站在屋前向里望:她正摸索着在堂屋里往外走,嘴里:“哎,哎”地应着,手里还拿着打了一截的毛线衣。
“哎呀,你还会打毛线衣啊!”我边说边来到她身边。
“崽伢子长得好不咯,我还冒看见过的啦。”
“还好呢,IJ带起克达。”
几年不见,当刮目相看。没有了当年的稚气,头发稍显凌乱,一身黑衣裤,打着的一截毛线衣看上去参差不齐,很大,显然是为她丈夫打的。可能是很久不见,也没想到我会突然来看她,她一时找不到话语,站在那里发呆。我也觉得找不到话题。寒喧几句,把给小孩的点心放到桌上,我就退出来。。。。。。
后来听说福伢子又生了一儿。她很凶,有“虐待”其夫之倾向。其夫死了,原因乡亲不好说,死了很久了。。。。。。
当我听说桥头上常常坐着福伢子时,我又有一种冲动,想去看看她。但是,这种冲动马上消失了:我见了她说什么呢?问她丈夫?明知故问,不好。问她儿子?从未谋面,不知从何问起。问她妈,我的救命恩人?我已到队上专程拜访过,也属明知故问,不好。问她为何坐在那里?这是很尴尬的问题,肯定问不得。问她可好?她会从何说起,告诉我什么?或许和那次一样,一时找不到话语,站在那里发呆,岂不是更加尴尬?与其那样,还不如不见,或许她认为我不知道她的现状还好些呢?
我固执地认为她还记得我,正如同我一直还记得她——桥头那个算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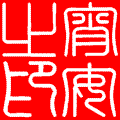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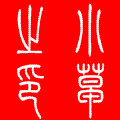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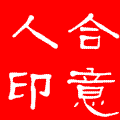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