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恋四十年,我终于拥有、但又不得不忍痛放弃的尘封往事
为保护个人稳私,文中全用化名
暗恋四十年
我有个幸福的家庭,妻贤子孝,我老婆比我小六七岁,在文革中我挨斗挨整最惨烈最痛苦的时后,十七岁的她风华正茂,是当地文艺宣传队最漂亮的小演员,追之者众,她却慧眼识人,不顾一切污言毁誉和所有亲友的反对,认准了我这个穷愁潦倒的“现行反革命”。六六年为躲避武斗,我返回长沙一个月,她不放心,竟单身一人冒险寻到长沙找到我家,足足等了十几天才见我一面,我亦为其深情所感。六七年十月,十八岁的她冲破一切阻力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她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我的最大安慰。
婚后不久我蒙冤入狱,我妻怀着身孕到处为我鸣冤申诉,七O后我儿子刚出世我即被冤判七年, 七一年我父亲因受我株连也被关进了牛棚(学习班),家中时常断炊,才二十二岁的她只好带着孩子返回乡下娘家,但娘家后母却骂她是反革命家属不许她住,要她滚出去。她哥哥本巳入伍入党提干了,也因受我株连而被清退出部队复员回乡种田,她所有亲友都劝她离婚,不少当地复员军官、帅哥、新贵都狂热地追她,但她坚贞不屈。她搬进一间乡下人家废弃的牛棚,不接受当地任何人资助,自力更生,从医院找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稚嫩的手日夜操劳,苦苦抚育着一双幼儿幼女。天热,乡下牛棚蚊子多,她双脚浸在两桶清水里,周围再点五六根蚊香驱蚊,劈竹棉签通宵达旦。当地才二十多岁的公社权贵因追她无望,竟协迫农村大队干部逼她与我划清界线、逼她与我离婚,甚至断她口粮,议价粮也不准买给她,她常常数月无粮,仅靠红薯萝卜度日,幸亏—些乡邻和好友给她一些粮票,她才死里逃生。她给狱中的我写信说,她决不离婚。她永远等着我。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入狱四年,也从末停止过抗争,天天上诉,在狱中戴着脚镣手铐唱国际歌,撕了判决书交入党申请,趁母亲来米江劳改农场探望之机从狱中夹带敉万字的“狱中来信”,我父亲连抄几夜写成几十张大字报贴上了市中心的五一广埸,轰动全城,不屈的斗争终于争来了市法院的复查,终于撤消原判予以平反了。
平反了,我并不为当地权贵所容,处处受挤压,连法院裁决的补发工资,单位都没补发给我(扣除牢饭钱后每月应补十三元),工作也不安排,一气之下,我只身返回长沙,拖板车、搞冷作、当水工,一无户口二无粮,什么苦和累都受过,最后病倒了,我妻闻讯,立即带着孩子赶来长沙,她再苦再累也要和我生死在一起,我们佃住南郊农家,她用一把菜刀两双手养活病中的我和孩子。
一九七九年,我父病故,我父亲单位同情我也欣赏我的文笔,同意我带工龄顶调到公司工作,并安排我当办公室秘书,我宁可当营业员不肯任秘书职,因为我不想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假话文章,单位只好要我搞业务。首先负责厂矿业务,我业绩显著。—年后经市商业局批准任命我为家电部副经理。任副经理二十余年,我年年销售数百万。这二十余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期。
乘改革开放之春风,我妻也在蔡锷路借钱租一门面做小百货生意,月入千金,三年还清了—切债务,制齐了一切家当,也支持了我任职期间能两袖清风。
多年来,我妻也太劳累了。—九九O 年,我关了正经营红火的小店。天下的钱是赚不净的,够用不欠账就行了。为了享受我热爱的生活,为了回报她数十年辛劳,我没要她再工作了,专门陪我出差,玩。
十年之中,我们游遍了名山大川,游遍了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北戴河,承德避署山庄、曲阜孔庙、上海苏杭、崇明无锡,广州、深圳、珠海,宝鸡、汉中、成都、重庆、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长江三峡、西安、洛阳、贵阳、黄果树、泰山、普陀山、昆明、西双版纳等等三百多个城市和名胜古迹,足迹遍于全国。
我妻之待我体贴入微,持家勤俭,待人贤淑,人见人夸。应该说我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跟我一样是初中生,但她是文革中的初中生,仅识字而已。我爱书如命,省吃俭用藏书近千册,基本都是古今中外名著,她—本也不看;我忧国忧民忧天下,她只认柴米油盐;如果谈文学谈诗词谈美术谈时事政见,她瞌睡沉沉毫无兴趣。她全部心血只倾注在我的身体和生活上。到晚年,可能是她一生受苦太深,她不信苍生信鬼神,天天念经拜佛,佛前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念念有词修来世,这似乎是她的全部精神寄托。生活情趣的差异,我真无可奈何。
其实我妻还不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折磨了我整整一生,也毁了我的一生,这是我终生难言无处可诉的痛。
早在六二、六三年我就读于某校时,有—位高雅漂亮的才女“甜甜”,其母是湖湘文化名人王湘绮之后,其母又是原上海华中美专齐白石的女弟子。名门闺秀的甜甜不但长辫垂腰,唇红齿白,美艳惊人,而且气质高雅灵秀,能诗会画,能歌善舞,同学中无不侧目,但甜甜只与我、苦苦(女)、骄骄(男)、四人亲密无间。我们天天在—起吟诗作赋、写生画画,那是多么幸福而短暂的青春岁月啊!当时骄骄狂热追甜甜,骄骄天生满头卷发,酷似普希金,英俊漂亮,也很有放浪形骸的诗人气质。骄骄的油画和素描都极好,尤擅诗词,家境亦富裕,市内有几栋私房出租。寒酸的我望尘莫及,我对甜甜只是视如蓬莱仙子,一直只在心中偷偷暗恋而已,倒是甜甜对我并不冷淡。
六三年秋我幸运地录取于重庆十三航空学校,入校即为上士学员,长沙仅招两名,命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我喜极之余在同学中四处报喜辞行,大家都为我高兴,甜甜知道我喜欢听她唱越剧,有一天还特地单邀我在岳狱山林阴深处为我清唱了一下午越剧。晚上正好上海越剧团来长沙演出,她又买来了两张票邀我去看越剧。从湘江剧院出来,深夜至凌晨,我俩漫步江边,清风明月之下,她目光灼人,真如凌波仙子。我万分冲动,真想拥之狂吻,但又担心名花有主。我试探地谈起骄骄有才有貌也对她有心,她淡淡地说骄骄怀才而狂傲,他可作朋友,但不可托付终身。她还说:有一次,骄骄想吻她,她瞪骄骄一眼,骄骄退之好远。我不知她这是对我的信赖?暗示?还是警告?我痴呆呆硬压住狂跳的心却不敢吻她,我甚至不敢主动去牵一下她的手,虽然我很想牵着她的手永远在月光下漫步。她却始终笑靥如花,无拘无束。(二十多年后她说那一天一晚她也终生难忘,她说当时她作了一个少女最大胆的种种暗示,我却有如呆鹅让她失望)。
第二天,苦苦又来约我江边散步,她默默无言又不肯分手,张郎送李郎,送到大天光,我们在江边月色中来来回回走了一个通宵。我告诉苦苦我喜欢甜甜,我写了一封表露心迹的信请苦苦转交给甜甜,因为我们四个人是最亲密的朋友。苦苦似乎泪眼汪汪点了点头,临别,苦苦塞了一封信在我手上转身跑了。
苦苦的信是用工整的小楷写在艺术信笺上,信笺上面还绘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景图,信的内容赤裸而火热,两年同窗,她说她己整整暗恋了我两年。她说她也看出我喜欢甜甜,但甜甜是骄骄的,她们早已两相情悦,等等。对苦苦我一直只视如纯真小妹,尽管苦苦也很美,有小鸟依人般可爱,我心中却只有甜甜。我当即草草复信—封拒绝了苦苦的爱,可能这伤了苦苦的心,其后苦苦竟休学不来学校了。奇怪的是甜甜也休学不来学校了。
当然我给甜甜表明心迹的求爱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女性求爱)也无回音,我强烈的自尊心被伤害极深,从此一别十年,我亦无缘再见甜甜和苦苦了。
当时我明明收到了接兵单位录取通知,又等了十来天,突然派出所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一下子我掉入了万丈深涯无边苦海。当时我只怀疑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六—年社教时十六岁的我在市委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时势座谈会上,我以赤子忧国之心坦言过:亩产几万斤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讲人民公社办食堂是大锅饭;讲全民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讲过苦日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彭德怀上万言书是为民请命。我怀疑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入档案、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承诺是假的。因这一切载入了档案而使我入伍被除名。人人都知道我接到入伍通知,即将要步入航空军校了,却突然被除名。我无颜去学校,更无颜见甜甜和苦苦,我难以承受这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双锤重击,一气之下我下了农村。
到农村后,我心如死水,—心只想过夜枕波涛.攸然诗酒的生活。一个月后,苦苦来信了,她讲因为我伤了她和甜甜的心,她俩都再未去学校了,(我不知怎么会伤甜甜的心,是我不该托苦苦转交求爱信?我更失望也更想念甜甜了,但我不敢、也无从打听)苦苦信中还说因我拒绝她对我长达两年的深爱,她恨我,她以为我是入军校要高飞了才拒绝她的爱,为了留住我,她要折断我的翅膀,所以她参与了一埸恶作剧,没想到真成恶果,害得我没去航空学校却下了农村,她也十分痛心和后悔。她已受到良心的惩罚,她非常痛苦。她请求我原谅她,她甚至希望我能回到她身边,她要用终生的爱来补偿我。她还说我走了以后,骄骄在狂热追甜甜,甜甜为躲避骄骄的狂追到某越剧团当演员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苦苦在我即将入伍前参与了什么恶作剧?我心己死,反正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既没深究也没复信苦苦问是什么恶作剧。直到文革中我被打成“小邓拓”,日批夜斗我不服,跳井抗争,党委抛出档案,我才知道是当年苦苦从甜甜手上骗到了一本我送甜甜的《诗草》,苦苦找到重庆十三航校驻长沙招录学员的某校官送了一些材料,除了《诗草》外还有一些落叶知秋之类的画稿,其中一副漫画头像下腭有—黑点,说这是影射毛主席下腭的肉痣,头象边有—草写的“周”字,也说是反写的“毛”字,(美校同学周跃下腭也有—黑痣,这是与周跃开玩笑画的漫画)而画纸背面却写了一首七律诗:“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
根据这些材料,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决书说我“一贯思想反动,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攻击三面红旆,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捕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唉,皆因情之祸引来报复,毁我一生。我受尽了种种非人折磨万般苦难,我全家人皆恨苦苦,但我对苦苦却恨不起来反而怜之惜之,对甜甜则思之更深,当然这是终生无望,高不可攀的暗思暗恋。
(因受字数限制,续下)



















 您的苦 他的苦. 苦苦苦. 好事总也论不到我!
您的苦 他的苦. 苦苦苦. 好事总也论不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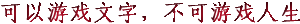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