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札记〉之5
在飞山脚下游荡
前言:由于在修怀化铁路时结识了长我几岁的共大知青P哥,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吸引我在72年多次从寨牙走路到飞山塘湖弯里,与P哥进行“精神会餐”。P哥是一中高65届毕业,学业优良,仅因家庭成分太高,与其他情况类似的同学一起被分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不能进入正规学校。其实,他们那一批人几乎个个堪称优秀,后来事业有成。例如:P哥是湘潭市民盟主委,韩少立是长沙市教委科研所所长,郑若敖是长沙市体改委主任,罗里林是长沙市粮食局副局长,欧阳松是中南大学教授、张丕淮是星港席梦司创始人等等。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潦倒不堪的知青。
72年2月26日、3月21日、4月13日、9月26日
前一段时间疯狂地游玩,在飞山,在甘棠......
......飞山令人想起奶头山,其形状就象一只突兀挺立的女性乳房。P哥的生产队就在山下不远的地方。队里总共有五名长沙知青,另4个是王国基、王擎柱、俞氏、菜牛。俞菜二人是65年下放的,三王是69年来的。P哥和王国基是同学,后者的妹妹也在本大队当知青。这二王有一个共同爱好:小提琴,没事的时候经常合奏一曲,其他人在一旁欣赏,倒也自得其乐......王胖子(擎柱)个头稍高,长得很壮实,还称不上胖,但年龄最小,有点吃亏,厨房里的事做得比较多,出工也很勤快......俞氏瘦瘦精精,不爱讲话,似乎和其他人不太融洽。倒是菜牛是个有趣的人,听说他读书不多,但他自称什么都晓得,什么都会做,总是吹嘘他有超人的能力。P哥拉起《重归苏莲托》他也跟着唱,就是转调时便开始乱坨......菜牛不太着家,一下就不见了人影,不晓得到那里玩去了,然后又突然出现了。“P哥,”有一天晚上他吹起了牛皮,“我可以走一部长途汽车一天的路。”“那不可能吧,长途汽车一天跑好远罗,你算过冒罗。”“我算下看——”可能他也觉得吹得有些大,“反正我一天走得400里路”。“是400公里不罗?”P哥故意逗他。他好象要证明自己有一双飞毛腿,裹紧身上的衣服,一转身就出了门,消失在黑夜之中......
弯里有一口非常著名的水井,叫“龙井”,也因此弯里的别名叫龙井庵,但我没看见庵堂。这口井水质极佳,水面很阔,可惜我一直没有到井边去看一下。听P哥说队里人把这口井看得很重,生怕有人弄脏了它。他们冒管那么多,在夏天酷热的晚上,几个人偷偷跳进井里洗澡......听P哥讲他队上的事情也很可笑。有一回队上开斗私批修会,发动大家检举他人的错误。然后有一妇女发言,称有一男人是流氓。这一下逗起了大家的兴趣,纷纷问她怎么回事。她有点害羞地说,这个人摸她的XX,大家故意问摸什么,冒听清,这位勇敢的妇女眼睛一瞪,胸脯一挺,大声吼道“mie mie!”......还听P哥讲了塘湖大队其他知青的故事,有杨葱、杨猴子、小劳、小维、欧阳松......
......他们花了30块钱买了20只鹅崽,当成宝贝一样招呼。看来他们对这群小家伙寄托了颇大的希望,使我想起“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俞氏打起了背包,到七八十里外的深山去烧炭,P哥基哥都发奋地出工。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一年到头有个好收入。......离上次来弯里还不到一个月,可是就有了一些变化。首先,他们的鹅长大了,而且夭折了一只,另一只被老鼠咬得变成残疾,不良于行。这只鹅菜牛给它想了许多自己发明的办法治疗,结果并没有起色,现在孤零零地挣扎在一只垫了草的箩筐里......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和XX、菜牛一道去了艮山口。正逢赶场的日子,艮山口窄窄的过道两旁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我们估计会碰到的新知青——关于他们的传说引起了我的好奇——三三两两地在拥挤的人群中钻进钻出。不过我马上失望了,我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那些打扮怪异、谈吐粗鄙的......“驴子”们。
XX打了声招呼,马上有三四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年走了过来。XX跟他们很熟,他问道:
“XX冒来?”这个XX是传说中的“驴子”之一。
“冒来吧?冒看见。”少年们四处张望。
我们在场上游荡。我发现这几个新知青的确具有传说中的那股味道,那股“教脑壳”味道。例如当有人的扁担不小心碰了他们一下,其中的一个马上就会瞪起眼睛,用教训的口气说“你的力气大些罗,担得起一个人罗?”或者在卖旱烟的大娘伙的担子里顺手扯两片烟叶:“试下你的烟力不力着。”公然的无耻,毫无顾忌,捣乱,恶作剧等等。在去他们队上的路上,XXX兴致勃勃地说起了他的一次历险记,说有一天晚上去偷桃子,被主人发现了,手持木棒要来打
他,狗凶狠地叫着。他缩在竹丛中不敢动弹,后来脚麻了,眼看支持不住了,于是他拼命地站起来,抓住主人在他头上挥舞的木棒一甩,转身就跑。后面主人、狗紧紧追赶,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他接着又说起另一个新知青,一次偷了人家8个南瓜,就用一双手抱着走回家......他们的房间里面很简陋,和学校寄宿生没有什么区别。我想回去了,可是XX不想走,菜牛知道他的心事,说:“你看中了哪一个,老弟帮你的忙。”XX用笑声否定有这个意思......
......在西街饭馆遇见了小维。我打量着他,他很自然地坐着。P哥问他:“最近画得有画吗?”
“画了。”他接口答道。
我和P哥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画了好几张。有一张是义和团的,乱杀,打做一团!有一张姚X拿帽子换去了,是几个妹子和几个伢子站在一起的。”
他很坦率,毫无隐瞒。
“写小说吧?”P哥又问。
“写了,‘迎春曲’。”他还是那么干脆。
P哥微笑着看了我一眼,似乎说“怎么样?”
我想起P哥以前说过的小维的一些事。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虚伪,非常自由。比如看电影,他不顾这是公共场合,大声唱歌;有时上街,就穿一条球裤,戴一顶破草帽,趿一双烂拖鞋,挎一只竹篮子。什么人情世故,礼节斯文,人言舆论,他一概无所谓。
“这几天不舒服,就在屋里搞了一些东西。”小维说着,忽然得意地叫道:“P哥,我两天另七气做了一百多分!”
“晓得罗,你讲了几次了!”P哥略带讥讽地笑道。
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安,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那儿去玩。
一走进他的屋子,首先跳入眼帘的是一副水彩画。我走近细看,不由笑出声来。色彩鲜明的画面上,三个身穿游泳衣的女郎懒懒地躺在沙滩上。身上裸露的部分充满着肉感。“为什么都这么肥胖?”我忍住笑问小维。
“不晓得,我画不得瘦的。”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我们又翻看着他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一卷画。说实话,他的画虽然没有什么素描基础,纯粹是勾勒轮廓,但他的想象力是丰富的,他还善于安排。
“这是艮山口的霞别,”他指着一张画,笑着说。
肥胖的身躯,短上衣,吊裤脚,下垂的双乳......这副画与墙上那三位女郎画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接着又看他的小说:迎春曲。他主动从箱子里拿出来的。
大概情节就是男主人公同朋友游岳麓山,与他在文革时要好的一位女子巧遇。这位女子深情又痛苦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原来她的父母要把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这时男主人公便鼓励他这位女友进行反抗,女子却绝望地叫道:
“我怎么能反抗父母的意志啊!”
是男主人公开始痛斥她的软弱、虚伪。女子只是默默地听着,大约她早已同意了这桩婚事,不过想扮演一下悲剧的角色。他们最后分开了。这时他的朋友呼唤他;他从同他一道游山的另一位女性身上发现了温暖清新的春意。小说就在一段对这春意的赞美中结束。
小维!我对他逐渐产生了兴趣。不是由于他的画,他的小说,而是由于他的无拘无束、天然无雕饰的性格。与他比起来,人们是多么虚伪啊!
......P哥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长沙去了。总的来说,他还是高兴的。人们总是对自己的行动抱着朦胧的希望,这希望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尽管有时是极短暂的。
后记:大约80年代的某一天,P哥告诉我,小维出车祸了。在长沙的大马路上,他与一辆汽车迎面相撞。奇特的是,他居然没受伤。他被车撞倒在地,司机惊慌<--EndFragment-->失措,众人围在身边。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一声不响,转身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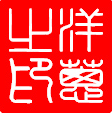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