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祖父逝世已二十九年了,但他的形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远去而在我心中模糊。相反与他老人家在一块生活的情景依旧清清晰晰、沥沥在目。每当回想起我的祖父,仍然会泪湿衣襟。
我刚呀呀学语,就是由祖父母抚养,直到七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所以在我的心里,任何时候装着的都是祖父母对我的疼爱,他们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都深深影响我的人生。
我的祖父生于1896年,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祖父家境贫寒,十二岁丧父,太祖母带着他和他的妹妹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为了养家糊口,祖父待他的父亲安葬后就拜师学木匠,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小小年纪要下水摸鱼,捉泥鳅,拾稻穗因而没裹脚。七十年代我回乡下,看到别的老婆婆都是三寸金莲,唯有我的姑奶奶是一双男人般的大脚板,甚是奇怪?问其原因,才知原故。
我的家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冲,山清水秀,民风纯朴。在这里文明与野蛮交识,科学与迷信共存,村民们几乎全一个姓,偶有极个别外姓也是招的郎。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不管贫穷富贵,年老年少都按辈份叫人,我的祖父辈份高,称呼他阿公、太公、老太公的都有。
说到我们山冲里的文明主要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读书识字的传统,不管家里再穷再苦,只要是男丁都要千方百计让其读书识个字。除开女人,几乎没有文盲,特别是老一辈的男人,有的虽识字不多,但毛笔字都还写得挺端正。当然家境好的大户子女有出国留学的,有读中国名牌大学的,就我所知,光在长沙几所著名大学里都有我们家乡的二、三级教授。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无用论,使我们家乡读书的传统几乎丧失,幸好改革开放又崇尚读书,尊重知识,家乡又源源不断地产生了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说到家乡的野蛮,在旧社会,甚至解放初期经常发生族群间械斗。这种野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造就了村民的勇猛、血性。听老一辈人讲,抗战时期,日本兵有一辆汽车出故障,停在路上检修,结果被家乡一涌而上的农民把日本兵打死,车子砸烂烧掉,等日本军队赶来报复,大家早已躲进了深山丛林,没有伤及身体半根毫毛。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将铁路修到了我们家乡的区域,但再也无法往前修建,因为遭到了家乡人民顽强的抵抗。日本人修一段就被毁坏一段,这种大无畏与日本侵略者对着干的精神不知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农民自发的?没有听到老一辈人说过。家乡这封闭的小山冲也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五四”时期就有在北京等大城市读书的学子回来号召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裹脚,打倒当时的旧政府,其中有被捕遭杀害的共产党人。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敢于与日本兵斗,却怕国民党军队,这主要是有些治军不严的国民党军队进村后,扰民抢东西,横蛮不讲理,抓年青人当壮丁,抓中年人当挑夫,不愿做挑夫的就要其家属用银元把他赎回,我的祖父也被抓去当过挑夫,但他随部队行走百十里路就逃回来了。所以只要是国民党军进村,村民都恐慌地躲进山林里不敢出来。也有治军严格的国民党军队,很受家乡老百姓的欢迎,我听祖父讲过,有一年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进驻我们村里,纪律非常严明,不抢不夺,连长亲自到老百姓家串门走访,宣传他们的军纪作风,并要老百姓向他告发破坏军纪的下属和士兵。国民党军队其实很穷,缺晌少粮的,由于不能抢,不能偷老百姓的东西,有的士兵实在饿得难熬,也有犯军纪的,有一个士兵偷了老百姓一只母鸡,结果被发现告到连长那里,连长当即集合全连士兵,并邀请全村老百姓到场,心情极其沉重地,当着大家说:“偷鸡者是我嫡亲的侄儿,由于家里穷,是我把他带到身边当兵的,他偷老百姓的鸡,军纪不容,立即检毙”!多少老百姓向连长求情,请枪下留人,但他还是没有留住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多少年来,每到清明节,家乡的村民都自发地为这个国民党的小兵扫墓,这悲美的故事在村里一代一代的流传着。
我的祖父也能识点字,基本上可以看通书信,他喜欢买观音菩萨的书看,闲下来就捧着观音菩萨的书唱歌似的读出声来,专一得将情神全都倾注在书中。在我的印象中祖父信迷信,又不信迷信,他不相信有鬼,也不怕鬼,他信菩萨、信佛、南岳他是要拜的,有一次去南岳拜菩萨,走到半山腰突然感到双脚沉重,爬山十分吃力,心里纳闷,不知是什么原因?自问难道是心不诚菩萨怪罪?待回到家里,方知是我奶奶正是在他拖脚不动的时候打死了一只老鼠,杀生了。祖父责怪完祖母后,告诉她“以后我去南岳敬菩萨,千万不要伤害任何动物,哪怕一只苍蝇”。
祖父木匠出师后,家境慢慢好起来,逐步逐步置了田产,建了新房,不过田大都是价格便宜的低产田,解放土改时已有六十担谷簿田,被划为中农成份。
祖父是一个特别讲情讲义,乐善好施的人。他常教我说:“要多行善,做好事,要富有同情心,多帮助穷苦困难的人,要知恩图报”。
祖父的一生是一个帮扶济困,助人为乐的人,是一个心襟袒荡不讲个人恩怨的人,是一个受恩必报的人,他从来不向我们说起所做的善事、好事,也不讲别人对他的伤害。他的故事都是家乡村民传颂的,所以我才知其一、二。
一九四九年底,大批解放军进了村,村民们不知是什么军队,又照样躲进了深山老林,后来解放军多次进山喊话,宣传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村民们才陆陆续续地下山回家。从此我的家乡开始了土改、斗地主、分田地。
我们村有一个地主,没有民愤,既不恶,也不霸,也不当家理事,只因家里田亩多,宅院大,他不爱读书,守候在家。当家的大哥及其他兄弟都是读大书的人,功成名就在外,属保护对象。结果他被镇压枪毙。行刑时他的家属都被关押看管,无人收尸。我的祖父默默地走进刑场,将死者崩散的脑浆都一一拾起放进他的脑袋,使之尸体完整,然后又独自一人默默地将尸体验殓掩埋。祖父的举动令围观的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都担心他会有一场大祸来临,哪知祖父仍执迷不悟,接下来的日子又为被关押看管的地主家眷们送饭送水。当时激进的青年农民强烈要求斗争我的祖父,但绝大多数农民反对,加之我父亲是解放军,祖父是革命军属而不了了之。
多少年过去后,我问祖父是否有这么回事?他说:“有”。我又问“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吗”?他说:“我既然决定要这么做,就将什么都置之度外了,做人要讲情义,要记住别人的好,受恩要报,尤其是恩人在危难的时刻要舍身相报”。我说:“这个地主家有什么恩于你呢”?祖父说:“我家穷,又孤儿寡母的,免不了遭人欺诲,这家财主常为我们讲公道话,扮禾时我和妹妹可随意到他们的稻田去拾禾穗,有时他还让家人割一把把禾穗送给我们兄妹。我的母亲是他的奶妈,我与他是同一母奶,奶大,就是兄弟,他家遭如此大难,我有责任尽自己的全部去帮助”。
四人帮倒台,国家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从政治中淡化,地主成份不再被专政歧视,被镇压财主逃亡在外的儿孙回乡寻根归宗,我祖父得知消息后,将他们叫到跟前,很郑重的将他收藏了几十年的,他们祖上的相片交给他们,然然如释负重长叹一口气说:“总算交给你的后人了!”,逝去财主的子孙们泣不成声长跪不起向我祖父谢恩,围观的村民们惊叹之余大发感概说:“如果时间还倒过去一年,公社肯定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我的祖父”。
其实在我祖父的脑海里并不知道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政治形势、阶级斗争。他只知道,人!不管什么朝代,什么形势,什么环境都要多做善事,不势利,讲情义,讲良心。
我的祖父木工手艺精湛,名传家乡数十里,慕名请他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年老了大活干不动,但一手装木犁的绝技让他无法闲下来,农忙时,农民们央求他装犁,就象城里的病人请求名医教授看病一样,排队等候,待装的木犁堆满了屋前屋后。工价是大家投其所好,给一斤自酿的米酒,一斤稻谷。我的家乡比较贫穷,一天难吃一餐大米饭。稻米、我祖父祖母舍不得吃,省下来送到城里接济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常感计划粮不够吃。我的祖父会医治刀斧之伤和其它见血的明伤,会止血。还会治一些疑难杂症,家乡人都称他是神木匠。我的祖父治伤治病是不收分文报酬的,有求必应,不管天寒地冻,天晴落雨,白天黑夜,只要有求就会立即上山采药,家里不备陈药,一律采用新鲜的草药,这样效果好,炎热夏天伤口不发炎贯浓。治伤治病的例子,为使文章不拖长,不一一例举了。
我的祖母讲“在旧社会,我们家从未过个好年,大年三十讨债逼债的人坐满一屋,是你祖父做好事,替那些无粮挨饿的人担保借粮,结果他们无力还借,就找我们要,我们也没有多余粮食,只好以祖父的名义写个借条,人家才肯走”。听说解放好几年后,我祖父还在陆陆续续替别人还债。
我祖父常闯荡江湖,在外打工,有时在外做工一年或几个月工都是空手而归,不是老板没有给工钱,而是他遇到了遭土匪抢劫受伤而无钱返家的人,就倾其所有相助了。
祖父说:“有两次遇到过贺龙率领的红军动员我参加,我也真想参加,但家有老母,只有我一个儿,旁无兄弟,无人替我尽孝,就没参加了”。
祖父不舍地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极乐世界,我常梦见他在那个世界过着自由舒心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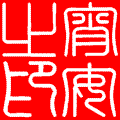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