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下乡的那年,雪真大呀!初下时瓦缝漏下的雪籽落在被子上,实在令人难眠,下了两天,到处盖满尺来厚的雪,总算可以睡着了。不是嘛,工不用出,整天都在烤炭火,确也清闲,早早睡下,做个好梦吧。
半夜狗叫声把人闹醒,墙缝里漏进火光。火光在移动,不是起火,不要紧,但捶门声却是对我们知青屋的。“驼医生,救命啦!”“什么事?”“我们是崖寨的,有人病得不行了,请你去看一下。”“公社卫生院离你们近些,怎么不去卫生院?”“他们治不了。”“他们治不了,我更不行!”“他们不肯去。”“他们不肯去,我为什么要去?”“驼医生,求你了,救救人吧!”显然我这不收钱的赤脚医生成了他们非要找的人。虽然口里不答应去,却穿起衣服,背上药箱,被火把队伍‘押’往崖寨,有人扶着,总算没有摔交。路上根据他们的叙述,我已判断病人是脑膜炎,果然体温表还没有插入口中,喷射性呕吐就弄脏了我的衣袖,只能送县医院!我一边给病人灌药扎针,一边安排他们扎单架。脑膜炎这个名词,大概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论城乡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他们知道我的安排必须服从,分发完预防药,他们就上路了。雪太大,他们让我不用跟着去。这时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呆在这寒冷黑暗安静的陌生农舍里。找不到食物,只好在火塘里添些柴,圈缩在角落里打盹,黑暗的雪夜是没有胆量一个人从陌生地方回去的。天亮边,终于屋里进来了人,告诉我担架上马路后,不用那么多火把,他来为我做早饭。“谢谢!不用,我就回去。”跌跌闯闯回到家,马上队里的社员都来奚落我。说不该轻易答应去出诊。“旧社会没有八十块大洋,这种天晚上哪个郎中会答应去。”“太不爱惜自己身体了。”不过,几天后再也没人开玩笑了,因为病人家从县城踏雪回来把信“脱离危险了!”队长黄狗牙大声自豪地强调来人没有回崖寨是先到我们团的。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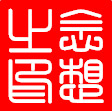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