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笔 艺术、理想与现实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与《五朵金花》是我喜爱的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可以说,许多城市青少年对于农村的最初认识就是从这两部影片中来的。这两部影片都拍摄于1959年,初映大约在1961年,人们刚刚从饥馑中走出来,在迫切需要填饱肚子的同时也渴望着色彩丰富的精神粮食。而对于我们这些将要走入花季的少年,影片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演员们如李亚林、金迪、梁音不知还健在否?即使还健在也应该年事已高了,但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却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一听到《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插曲,我的眼前就象过电影一样清晰地浮现出四十多年前银幕上的情景:女主人公从丰饶的田野走来,攀上新架设的电线杆,随着悦耳的旋律和歌声响起,我们眼前呈现一幅幅秀美的画卷: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
杏花村里开杏花,
儿女正当好年华。
男儿不怕千般苦,
女儿能绣万种花。
人有那志气永不老,
你看那白发的婆婆,
挺直了腰板也象十七八!
电影《五朵金花》的放映更是激起了我们对边疆的好奇和向往,阿鹏与金花的对唱,唱红了大理、蝴蝶泉,唱红了洱海苍山,直到如今的云南旅游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影的宣传。那些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的曲调和歌词,大部分人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
大理三月好风光哎,
蝴蝶泉边好梳妆,
蝴蝶飞来采花蜜哟,
阿妹梳头为哪桩。
……
然而艺术与现实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几十年后,史料告诉我们,这两部影片赞美和歌颂的“大跃进”时代远不如影片宣传的那样美好。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反映的山西农村,在“大跃进”时期是个“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的地方,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几十万劳力上阵,建几万座小高炉“大炼钢铁”,搞得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粮食减产、民不聊生,哪里是电影描写的那样美不胜收,直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生态环境都难以恢复。
至于《五朵金花》的家乡云南省,艺术与现实的距离就相去更远了。电影中描写了五位白族姑娘:副社长金花、养猪金花、积肥金花、炼钢金花和拖拉机手金花,在那些火热的场景后面掩盖的是违反自然规律和科学法则的现实。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从原始社会一步就跨进了人民公社。队队办食堂,因为居住分散,社员们要翻山越岭去食堂吃饭,因为饥饿,常常有老人、小孩、病人倒毙路旁。为了办万头猪场,把家家户户的生猪都集中起来喂养,结果造成大量死亡减少。为了推广拖拉机,把农民的老式木犁都烧掉。为了积肥,就把农民的老土房都拆了做肥料,使许多人无家可归。为了大炼钢铁,就乱砍树、乱挖矿,因为做风箱要用大量的木板和鸡毛,就把老百姓的棺材征用、把社员养的鸡杀了拔毛。在云南这样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当时仅有一千多万人口,大饥荒时期的两三年中竟然饿死了几十万人,甚至发生了多起人相食的惨剧!许多边民试图逃离饥饿的魔掌,却被以“暴乱”、“叛国”等罪名被镇压、被抓捕、被剥夺生存的权利。而当时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谢富治不仅没有挨批评,反而官运亨通,不久就被上调进京,担任了公安部长,成为MCD整人的得力干将。直到他死后的1980年,才因为他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而被开除党籍。至今为止,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一级、哪一位领导人为“大跃进”、“大饥荒”承担责任和受到处分,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的隐瞒和封锁,有的只是对天老爷和苏修的谴责:“过苦日子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不久前有朋友推荐给我一部名为《墓碑》的纪实文学,我从中读到许多从不了解的史实。
不要过于责备作家们违背真实、粉饰太平,就在这两部电影拍摄前两年,不是有几十万良知未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吗?真理在强权面前往往只能退让,独裁者需要的是歌功颂德的吹鼓手,但愿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
但是,尽管明知并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仍然深深喜爱这些影片和歌曲。正如有人评说:“虽然现实是残酷而痛苦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影片中体会理想主义年代的火热激情,集体生活的无私美妙, 劳动建设的单纯快乐, 青春和爱情的热烈、甜蜜、美好……那无一不是我们不能缺少的体验和情感,尤其是当一切都已遥远。”
我想,这就是艺术超越现实的魅力,这就是经典作品受人喜爱、经典老歌传唱不衰的原因。身居凡世而心想天堂,人类总是追求着比现实更美好的理想,并将理想寄寓于艺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让我们真正生活在并非虚构的诗情画意中。
<P align=center><EMBED style="FILTER: Xray"
src=http://wma.fashaodie.com/music_03/136/06.Wma width=300 height=30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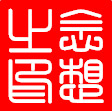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