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乡那天,我们胸前都挂着大红花。那花,虽是用纸扎的,也很灿烂,把我的白衬衣映出一团淡淡的红晕。车站广场上涌动着上千朵大红花,就像一片片鲜红的朝霞。那些天,我一直有些云里雾里的,“革命青年”、”、支农先锋”、“新型劳动者”等一顶顶笼罩着美丽光环的高帽子全飞到我们头上,我仿佛一下子被人抬到了天上,月 台上纵有沉重的话别声与凄凄的啜泣,我也顾不得了,男儿有志当走天下,我激情亢奋地跳上火车。车厢里盛满了歌声和笑声,青春的旋律盖过了火车隆隆的轰鸣声。 胸前的大红花一路上陪伴着我,从喧嚣的都市,一直走到都庞岭下的一个青烟袅袅的小村落。
县里派去接知青的干部将我们那个地方形容成“抬头柚子打脑壳”,尽管夸张了一点,但在湘南农村来说,也算 得上是土肥水美的富庶之乡了,有两个队的工分值竟在九角以上,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可惜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今日抓典型,明日割尾巴,村子里闹得鸡飞狗跳不安宁,社员们折腾一天下来赚不到一包烟钱。我们朝出暮归,每天为这一包烟的代价而鞠躬尽瘁。几年下来,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桃川土话,挑得动百多斤重的担子,会扯稗草、会挖芋头,还会端着粪箕站在水田里撒石灰,九个年头过去,我总算熬到岸了。
离开小村那天,我除了手里拎着几件换洗衣服,背上还背着个大南瓜,南瓜是队里的老鳏夫玉圃伯爷送给我的,这些年来,我常和他一起在河洲子上放牛,临走时,他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就从园子里摘了这只大南瓜送给我。
我穿着九粒坨坨扣子的粗布衣,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草帽虽然被太阳晒得泛白,帽檐上“踏遍青山人未老”几个字仍依稀可辨。走出长沙站台,我将背上的南瓜放在地上歇 一阵,久违了的车站广场上,依然熙熙攘攘的,我心头一热,就觉得隐约有号鼓声传来,冬冬鏘鏘、抑扬顿挫,还有鲜花、口号声……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正沉思间,有人朝我走来,是一个胸前挂着大像章的老后生,“……这不是我们班的诗人吗?”我读初中时,曾写过一首歪诗被老师拿在班上念了,几个同学硬是将我抬上了诗人的宝座。我打量了半天,才认出他就是当年躲避下乡的那位老同学,老同学掏出锡皮纸包的“飞马”,很有派头地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你那烟我烧不惯,从兜里摸出个烟荷包就卷喇叭筒,他笑了笑,又上上下下将我端详一番,意味深长道:你不是去改造农村么,怎么反被农村改造了?”老同学已是一家工厂的工宣队长,是场面上的人了,他得知我的户口已迁回,劝我先不忙找工作,“最好到土方队挑两年土,把皮鞋、手表置齐了,再找关系活动一个大单位。”说罢,拎着个漂亮的旅行包器宇轩昂地进站了。
天色几乎完去全黑下来,不知为什么路灯还没亮,我背着大南瓜,沿着曾经很熟悉的大马路朝前走去……
{学打字,摘自《凄惶的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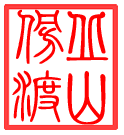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