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当知青以前还不懂什么叫帮工。
那天下午,队长保云对我说:“你去帮信国叔砌屋。”
“不出工了吗?”我问。
“就算你出工。”队长抛下一句话自己干活去了。
我来到信国家屋场,只见有好些队上的人已在帮忙。他们有的运砖,有的上梁木,吆喝喊叫,快乐得像在过节。我开始是挑砖,土砖二三十斤一口,挑了一会就有点累。信国叔看我身长,要我去丢砖。我打篮球还可以,但要把大土砖一口口丢上屋却不容易。好在乡下的土砖屋不高,更好在人多热闹,玩笑加粗痞,半天一晃就过去了。
我在水桶里马马虎虎洗了洗手,正准备回去。下屋的本爹喊道:
“莫走,有饭吃。”
果然是有饭吃,几个汉子和信国的伢崽抬出了两张大桌,信国的堂客莠婶子笑嘻嘻地正在往桌上端菜。本爹手一挥两声“上桌、上桌”,便一大屁股坐到了板凳上。桌上辣椒、酸菜、面条(面条也是菜)加起来也有八大碗,最抢眼的是一碗炕肉。炕肉就是熏肉,乡下人杀了猪,把它挂在灶屋的梁上,整日被柴火烟熏着,想吃时就割一块下来。那肉红黑油亮,人见人爱,确实惹眼,何况是在那个年月。
“小刘,来来,添饭添饭。”本爹见菜齐、人齐便一边自己添了一碗米饭,一边招呼我。这桌饭虽无水酒,可有白米饭就不错了,因为那时我们的饭里是要放许多茴(红薯)的。
“小刘,来来,莫讲客气,夹菜夹菜。”也许本爹见我新来乍到,才特别喜欢招呼我。我当然还是要讲客气,等几个人动了筷子我才伸手。
“来来,吃肉吃肉。”本爹又在发令,众人的筷子便伸向了那碗炕肉。我有点不习惯,甚或有点反感,干吗吃饭吃菜也要统一行动呢?于是我偏不去夹肉而去夹萝卜,等吃了萝卜又吃了一口饭才将那砖头样的大块炕肉夹到口里。
可是,还没等我咬断“砖头”,本爹又“来来”地带领众人攻向了炕肉。莫说我不能一口吞下那块肉,就是吞下了我也不会跟着他的号令行事。我依然我行我素,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吃肉吃饭然后再夹第二块肉。
谁知紧跟着本爹就带来了众人的筷子。我有点奇怪,干吗那么着急,干吗跟着我呢?
第三次夹肉时,我的筷子和本爹的“来来”几乎是同时达到炕肉的碗边。当这一轮攻击结束时本爹发出了一声“噫——”,于是,八双眼睛都看见了碗里还剩下一块肉。我终于明白了,主人招待帮工吃肉是“计划经济”,每人四块,桌上由年长或有格的人发令,便是为了不出错……显然,是我少吃了一块肉。
“嘻嘻,多了一块。”等我弄清这点时,本爹已经把那块肉塞到了自己的口里。他瞟了我一眼发出几声含糊的笑。本爹面前的调羹上清清楚楚地摞着四块一动未动的大炕肉。我愣了一下,本爹的眼中分明有几分狡诘,又分明有几分孩子气。我赶紧把眼睛挪开,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他家的三个孩子,大的在上小学,小的还在穿开裆裤。他的老婆体弱,他是不得不又当爹又当妈,家里破破烂烂一塌糊涂……
散席了,本爹不再喊我,径自回他下屋的家。他用一根筷子串起那四块肉,举在空中,嘴里哼着乡气十足的花鼓调,一蹦三跳地踏上那细长的田埂,走进傍晚的彩云……
以后我又去帮过工,吃过肉饭,但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许多年过去后,我只记得这次帮工,只记得本爹“来来”的号令和他举着炕肉融入晚霞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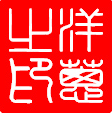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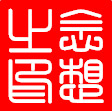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