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前的今天
张老三在湖知网华容知青家园发帖问:元月八号是什么日子?
1969年元月八日对于长沙市二中最大一批赴华容插队落户的我们来说,是一生中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从那天起我们成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以后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深深地烙下了“知青”两个字的印记。四十年了,我们人生历史上很多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忘记了,但元月八日却怎么也忘不掉!响应张老三的号召,重发我的《下乡第一天》以示纪念。
40年前的今天即1969年元月八日清晨, 在沿江大道小西门客运码头,在一阵阵锣鼓、鞭炮声中,长沙市二中第二批去华容县插队落户的同学登上了一艘大客轮。我们挥手告别了欢送我们的亲友和师生, 告别了故乡长沙,告别了黄金般的中学生活,踏上了我们这一代人新的人生旅征。
轮船沿湘江而下,船舱中充满了欢歌笑语,不少同学们还以为大家一起乘坐上了这艘轮船,不是到艰苦的农村去插队落户当农民,而是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去欢快的旅游。大家不停地唱着歌,从全船所有人参与的大合唱,到一群人的小组唱、个别人的独唱;从唱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各种革命歌曲,如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等外国革命歌曲。有些同学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们在思考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难道真要去当一辈子农民吗?我们这一代人今后的人生命运又会是怎样呢?茫然、无助,有的同学甚至躲在一旁暗中流泪、哭泣。这时有的同学唱起了令人伤感的歌曲,如“我离开了我的家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轮船过洞庭湖,逆长江而上,经过整整一天的航行,晚上到达了华容县的洪山头码头。我们原想:毛主席发号召了,在岸边应有不少贫下中农在热烈欢迎我们到来,但岸上热闹场面没见到,四周静悄悄,黑漆漆的一片,只有当地几个公社、大队干部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在迎接我们。
我们被安排至砖桥、东山几个公社插队落户的同学下了船,便由他们分别领至各自所插队的所在地。
我们去集成垸的同学由几名农村干部带领,在洪山头码头又上了一条大木船。木船沿长江上行到了集成垸,沿途分别由垸内各大队派人带领下放到本大队的知青上岸,再领我们分别步行到各自落户的生产队。我和六位男、女生被分配到红旗大队八生产队。生产队已派了一位年龄比我们稍小的社员来接我们。
接我们的小社员赶了一辆“牛拖车”用来给我们装行李。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集成垸的这种牛拖车,是一种没有车轮的牛车,样子很特别,就象我国东北地区冬天滑雪用的雪橇,但拖车的木架比雪橇要高且笨重。这种牛拖车是当地很实用的特有运输工具,集成垸是长江泥沙淤积形成的平原,道路泥泞而无石块,牛拖着木架上的货物比较平稳,也便于在泥泞的道路上滑行,还可在水田里拖运农作物。
我们几个知青对牛拖车并不感兴趣,却对在城市很少见的水牛感到很新奇,大家都争抢着要骑牛。我与宋同学抢着爬上了牛背。这是一头很温顺的老水牛,它不用牛的主人牵引,驮着我们两个男知青,拖着拖车自顾自慢慢往前走。老水牛能识别回家的道路,不知不觉在黑夜中走了好几里路。我们发现接我们的社员和其他知青与我们距离相隔得越来越远了,四周又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耽心会迷路,想让老牛不走了,又不知要如何使唤才能让牛停下来,急得我们对着老水牛直叫:“停下!停下来!”老牛可听不懂我们的“长沙话”,仍埋头只顾赶路。老牛老老实实把我们一直送到了第八生产队的禾场上才停下不走了,它知道到家了。这时已是深夜,我们六名知青被临时分散安置在几户农民家中睡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清脆悦耳的童音歌声唤醒了,谁这么早就在练声吊嗓子?起床出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少年拉着一头大水牛在唱着“也荷也荷,也荷也荷也”的小调。后来一问农民才知道,冬季为了不使水牛将尿拉在牛栏内弄湿了稻草,清晨农民要将牛拉出牛栏外,唱着“也荷也荷” 的“催尿歌”,催促着大水牛赶快拉尿。我想到了在长沙一些父母给自己的小孩催尿时也唱“催尿歌”,但那声音太单调了,真没有这位小孩对老牛唱的这么动听。
刚到生产队时,我们被安排到生产队各农户家轮流吃“派饭”。第一天是在雷队长家吃“派饭”。早上,我们“学生伢”用牙膏、牙刷在嗽口,引来一些好奇的小孩在一旁看着我们,不知我们这是干什么。雷家嫂子热情用脸盆盛了一盆热水给我们洗脸,第一位同学用这盆水洗过脸就将水倒掉了,雷家嫂子见另一位同学又端着脸盆去厨房盛热水,她用很惊讶的脸色望着我们。后来我们才明白,在当地农村一盆热水却是给全家大小洗脸共用的。
难道住在长江边还缺水用吗?饭后我们要为雷家去挑水,便问雷家嫂子取水井的地方。她说就在屋前面的水田旁。我们到那儿一看,水田旁有一个小水坑,水虽清亮,但与水田相连。这难道是“井”?这水怎么能吃?于是我们挑着空水桶要去取长江水。我们翻过大堤向长江边走去,长江已处于枯水期,我们踏着泥泞走到陡峭的长江边。在我们印象中的长江应是一条清彻的大江,可是当看到带有大量泥沙的滔滔长江水时,我们感到非常失望。这难道是我们曾经仰慕的长江,我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站在了黄河边上,我们挑着这一担混浊、饱含泥沙的江水,这长江水和黄河水又有什么差别?!
白天,我们在生产队走了一圈,整个村庄显得异常宁静,只见到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原来青壮年劳力都到长江改道的工地上“开河”去了。农民们的住屋散落在大堤旁,大多是低矮的茅草屋,这种屋是用芦苇糊上牛屎泥巴作墙,用茅草遮盖屋顶,屋里面阴暗潮湿。只有少数条件好的农户住上了土砖屋,但面积都不大,也只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当初我们选择到湖区来当农民,是听说湖区农民生活比山区要富裕。可是见到这里的农民居住生活的条件这么差,感觉长沙周围的农村条件要比这里好多了。
晚上,我们三个男知青搭了个床,就睡在雷队长家堂屋中。在这天晚上我们迎来了在长沙市极少见过的一场大风雪。我们醒来,发现我们被子上复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早晨我们来到大堤上,望着茫茫白雪复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想到这片大地就是我们要长期生活的地方,我们在长沙的那种高涨的热情也随着这场大风雪冷却下来。面对现实,大家不得不思索当初自己到农村来的决定是否正确,不得不考虑今后在农村的生活和自已的命运前途。
这时雷队长找来几付扁担和箢箕,递给我们几个男知青,说要带我们到长江改道的工地上去参加劳动。就这样,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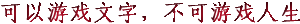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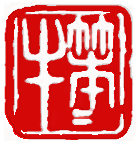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