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为人父的喜与忧
乐 乎
27年前的今天,女儿来到人世间。弹指一挥间,27年过去了,但27年前的那一幕,仍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
窗外,夜已深沉,万籁俱静,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鞭炮声,显示着春节的气息。大年初一深夜,萍突然肚子疼痛,脸色惨白,直冒虚汗,出现分娩的预兆,我慌慌张张提着早已准备好的什物,背着她直奔职工医院。
门外北风呼啸,路灯昏黄,天上稀稀拉拉下着小雪,到处白雪皑皑,路上结了厚厚的冰。为了防滑,我给鞋绑上布条,小心翼翼地背着萍,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位于山腰的医院。因为过春节,职工医院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工友在值班,我急忙让工友去叫医生,又赶紧找来几个煤炉生火。萍无力地靠在凳子上,冰凉的泪水随着一声声呻吟顺着脸颊流淌,虚弱得象一团棉花,忍受着上帝赋予母亲繁衍后代必须承受的痛苦,几乎要虚脱过去。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吓坏了,左等右等也不见医生,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护士,萍才进了产房,躺在病床上,她闭着眼睛咬着嘴唇,头在枕头上不停地左右摇摆,强忍着临产前的痛苦。我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萍的头,紧紧住着她的手,喃喃呐呐地讲一些坚强女性的故事。终于,“哇”的一声,一团蜷曲的,颤抖着的,带血的小生命诞生了,我抬头看看钟,时针正指初二的凌晨4时25分。这一声“哇”,给冷冰冰的产房平添了无限生机,初为人父的快慰和幸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护士将孩子洗净送到我手中,我端详着女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凉了半截。只见女儿皮肤红里泛黑,满脸皱纹,单眼皮,塌鼻子,厚嘴唇,脑袋成不规则形,头发稀疏且泛黄,奇丑无比,象个小老头,父母亲优良基因不沾边,缺陷却全占了。天哪,这模样以后如何嫁得出去,我不由得为女儿今后漫长的人生岁月而忧心忡忡。
更为忧虑的是,我乃一介翻砂普工,既没有过硬的后台,又没有显赫的背景,不可能为她的成长提供任何优越条件,女儿的前程全靠她自己了。女儿如果没有出息的话,弄不好将来只有顶替老爸,继承衣钵,做新一代翻砂工的路可走,象厂里许多职工子弟顶职一样。想到她今后可能象我一样受苦受累,越想越寒心,几乎后悔生下她来。
我将女儿放在萍身边,萍已经睡着,她太累了,伟大的母爱使她在睡梦中还露出幸福的微笑,仿佛沉浸在爱与诗的意境中,母女俩睡得那么安详,睡得那么香甜。我站在床前,凝视着她们,深感为人之夫为人之父责任重大,我捏紧拳头,暗暗发誓,为了女儿的幸福,我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起码得混个班长或段长当当,在女儿面前树立起高大的形象,让女儿可以骄傲地在同伴面前宣称:“我老爸是翻砂车间的班组长,管十几个人哩!”
急就于初二凌晨女儿出生日
女大十八变,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象她这般年纪,老爸还在田里摸泥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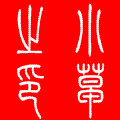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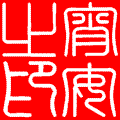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