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年谱
——我和堂客的那些“七俚八俚”的事
(一)
公元1964年秋天,中华大地刚熬过三年饥饿的日子,却又迎来一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暴风骤雨,成千上万的城里伢妹子,刚刚开始有口饭吃了,又要卷起铺盖,离开最疼他们的爹娘,到农村去种田安家,一个折腾接着一个折腾,老百姓总难得安生。也就在这莫名折腾中,我第一次认识了我堂客。她带着她的清纯娇小,走进了我的世界。
认识我堂客,首先得感谢伟人的上山下乡,没有伟人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是不会认识堂客的,也不能将她“追到手”的,我俩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父母的饭碗不被“打烂”,为了弟妹们还有口饭吃,报名下乡,而走到一起来了。因为此前我们的爹娘已被领导找去“谈话”几次,次次都将“碗边”敲得嘣嘣响,我们只得赶快卷铺盖走人。
我们四男四女背着被盖,来到这深山竣岭的小山村,山冲口上,只有俩户人家,一户农民,一户就是我们,生产队的农民们,都住在山外几里远的地方。山冲口的这俩栋陈旧的土墙屋,在秋风秋雨中,就显得格外凄凉。就在孤零零的那栋土墙屋里,俩条板凳搭上一块木床板,铺上被盖就成了我们的家,乌鸦凄凉的叫声在空旷清冷中久久回旋,阵阵揪心。常使我们泪眼婆娑,夜不能寝。当冷清的秋月悬在这深山山头时,木板床上的我,望着小窗外的冷月,常涕泪满襟。崇山竣岭的冷凄,总叫我们倍思父母倍思家------。
那年我们十六岁。
在高山竣岭的日子里,四男四女只有我和堂客历经磨难,九九归一,终成眷属。另三男三女却无缘而散,各奔一方。所以哥们都说我“懂事”早,“骚劲”足(对爱情的憧憬),我又为何"懂事"早,“骚劲”足呢,仔细想来;全源于我少已更事,读书求学时,不好好读书,整日里捧着托尔斯泰,狄更斯,萧洛霍夫------流连忘返。我幻想着和阿克西尼亚的初恋,(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女主角),迷恋着度拉的纯情(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女主角),钟情于娜塔沙的爱(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女主角)------。她们使我早早“懂事”,憋足了“骚劲”。现在想来,却无怨无悔。当我们眉目传情时,是她们帮我读懂了堂客的“眼语”,感受到彻骨的爱,除了感谢伟人,我还得深深的感谢这些欧罗巴的文学巨匠,是他们把“骚情”和浪漫,带给了一位远在东方,华夏湖湘的情窦初开的“小小少年”。
在青绿满坡的小山冲的小路上,赶闹子回来的我们,在春风暖日的柔拂下,心旌荡漾,小鹿撞心。我第一次情不自禁的搂抱住柔弱娇小的堂客,送去我的初吻,搂抱中的堂客在我的怀中浑身战抖,当我忘情的去亲她时,她突然发出一声大叫,赫得我一弹,情趣全无,我松开手,轻轻的问她何解,她红着脸,呢喃自语;我也不晓得何解------。春风暖日下,我刻骨铭心的初吻没送成,但我一世记住了她的温柔,她的发香,她的羞红。
那年我们十八岁。
我实在是一无可取的人,一对绿豆眼,俩片大肥唇,其貌不扬。由于发胖,赘肉猛生,俩只绿豆眼已被脸上横肉挤得只剩一条“缝”,所以至今堂客还在念叨;你那双绿豆眼禾解越来越细,还能看见东西麽?-------。我一不会干农活,常遭贫下中农斥责和讥笑,二不会做饭菜,洗衣物。至今都只会烧开水,碗都不会洗。三不会吟诗作画,吹拉弹唱。四不会察颜观色,呆头木脑,不善言词。“文”又文不动,“武”又武不得。禾解堂客又会看上我呢,百思不解,唯有俩字可解;缘份啦!这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哦!
在山冲里的日子,懒得洗也不会洗衣物的我,总是将脏衣脏物到处乱扔。人也臭哄哄的。堂客总是千方百计的将我的邋遢衣物,寻去洗晒。然后整整齐齐的放在你床头,眉眼之间,开始流光溢彩,传情寄意了。从相知相恋,我和堂客经历了近十年的路程,终于结为夫妻。这期间,也有几位女子向我眉目传情,我却毫无感觉,堂客已将我心装满夯实,旁人已无法取代,在我眼里,堂客是最美丽的女人,那大大的眼睛,樱桃小嘴,窷窕身材,活脱脱就是一副美人图,叫你永世难忘,而她的执着,她的真诚,她的温馨,已能将你完全融化。
堂客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执着刚烈,为人处世就是一根筋;容不得虚假,只来得真。堂客至今从不涂脂抹粉,描黑涂红。也从不“穿金戴银”,既无金戒,又无银链,唯有纱巾俩条御冷挡寒。她从无这点嗜好,永远的素面朝天。可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哈”堂客依然最美丽。
公元1975年的秋天,我终于从冷凄的山冲里,经过伟人的“考验”--“折腾 ”,又回到喧啸的城市中,于是, 我们在河西二里半,湖南师大庄严肃穆的门楼下,矮遢遢的一座茅屋里结婚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床,有了自己的家。虽然还是租用别人的旧茅屋,堂客却好高兴,十年的相恋,十年辛酸的等待,十年金贵青春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那年我们二十七岁。
三年后,我们有了自己最心爱的孩子,承载着我们所有的爱。走进了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俩成了我们仨。
那年我们三十岁。
(二)
二十多年前,正是不惑之年,一日,华灯初上时,办公室里依然雀战正酣,全然不知下班已多时,正当开和之际,接一电话;“还在干麽子,还不死起回,麽时侯嗒------”,一女中音威严而冷竣,
“来嗒一客户,我在加班呢------”,我慌乱中又回此一句。
“加你的脑壳,加班---”女中音开始咆哮了,
“你是那个咯,------”我已乱了阵脚,语无仑次了,
“我是你堂客,还那个那个------”。女中音大声咆哮。“你跟我赶快回家,再不回,我可要到你公司掀桌子,吵棚嗒------”“呠”的一声,不由分说,已将电话挂断。接下来,我立马离开牌桌,恐恍中在哥儿们的讥笑声下匆匆回府,面应堂客的“加班”之问。
自迷上这千古之“柳叶戏”——麻将,已走火入魔,废寝忘餐,常通宵达旦不归家。为了应付堂客的怀疑,常满口谎言,只求搪塞过关,相安无事,以至亲朋戚友,哥们伙计的爷爷奶奶,三姑六姨的“红白喜事”,基本都办遍了,稍不留神,有的还办了“俩次”。堂客已基本不信“加班,帮忙”之言,因为她几次遇见“仙逝”的哥们伙计的“ddjj”------。
一日搓麻又一夜未归,次日中午才恋恋不舍的离开“战场”,头重脚轻的蹒跚回府,轻轻的打开房门,想溜到床上酣睡一番,却发现堂客怒目圆睁的立在门前,我实已黔驴技穷,只得“张口现来”,还未等我讲完,“拍”的一声,重重的一巴掌已打在眼角上,眼冒金花,立时满眼都是“五坨六索”,整个眼角都乌青的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脾气最随和的人,最有绅士风度的人,从未骂过堂客半句,打过堂客一下。堂客亦从未打骂过老公,一张“五好家庭”的标牌,钉在门口已有好几年了,邻居们都称道我们“好夫妻”。所以这脸面丢不得呀,为怕邻居们听见,我捂着脸,毫无声息的忍受下来。默默的接受堂客的惩罚,我能很理智的立时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全是我的错,记得有二次通宵雀战之时,突然我手里捏着一个“二坨”,不声不响,俩眼发呆,身子从凳上直滑到桌下,人事不知,哥们都慌了手脚,连忙送往医院抢救,才从“麻爷”处将命领回。至此,堂客是日日挂念,时时揪心,提心吊胆的念着各杂不省心的“麻老公”,堂客是在心疼我。这一巴掌,道出了堂客殷殷关切之心。该打!
以后上班的日子里,在哥们含蓄的关心中,我只说是不小心碰了下眼角。保住了脸面,也保住了山野恋出来的感情。熬过了这长长的十几天。自此以后,开始慢慢的远离这“柳叶之戏”,时至今日,再无记挂这烦人的游戏,这一掌可谓刻骨铭心。
那年我们四十二岁。
( 三 )
“喂,你还在那里咯,何解还不回,饭菜都凉嗒-----".一女中音焦急而烦人,“我已在车上嗒,还有半小时就到家,莫等我嗒,你先恰------”。打开手机,才发现堂客已数次来电话问询,关切之情,溢于心间,此时我和堂客已快进入花甲之年。我出门办事,散步,袋里的手机天天都要响数次,已不是当年查岗麻战,威严冷竣,而今字字句句已成温馨关情。
堂客于九十年代提早退休,人生的下半场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进入五十几岁后,堂客开始发福发胖,大眼睛也开始流出茫然,整日里离不开电视,常叫晚上睡不着,美人儿成了烦人儿。尤为不能容忍的是开始“罩昂”嗒老公,无事没事的念叨他,数落他。当着亲朋戚友,哥们弟兄的面,念叨着老公的“窝囊无能”;“他晓得麽子咯,你信他的,会冒得“早饭米”-----”可至今她还冒说过;信他的会冒得“中饭米”。她晓得;话莫讲绝嗒,说不定,那一天,各杂“哈”老公兴许捧杂“诺贝尔”回呢。
为了nba,为了姚明的“上海午步”,俩公婆常闹得不可开交。几年前为看奥运,就不得不买俩台电视,她看大的,我看小的,互不相干,各得其乐,平安无事。前响坏了一台,于是又爆发一场“阿以”之战,一个摇控器争来抢去,又“翻脸”不认人,接下来就十几天不讲话,不理人。直到老公热脸贴冷屁股,连撮带哄,才恢复“邦交”。
堂客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她虽然极力数落老公,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她,她又时时天天记挂着老公的平安顺畅。其实我是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从心底里赞成女人半分天下,可是在现实中,女人还是从属物,女人始终还是块“地”,男人才是种地人,地和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如今“地况”虽好一点,也只不过是蒙上一层厚厚的“火土灰”,如此而已。堂客之心我非常理解,爱莫能助也。堂客的念叨,数落,如今已成家常便饭,无奈中我将她归于更年期的发作。几十年的“情累”。虽然嘴“狠”,可心却万般柔情。也应了那句;刀子嘴,豆腐心。
人生的下半场已悄然拉开帷幕,相濡以沐四十余年的堂客,虽常念叨数落老公,但我依然记着她的柔情,她的真诚,她的执着。虽然从我们相识相恋,几十年来我们嘴里从未说过“我爱你”。但我从心底里感到堂客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最疼我的人。
满装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我和堂客携手走进了六十岁。
几十年来,堂客枕边的鼾响,成了我入睡的“摇蓝曲”。 没有她在枕边的鼾响,我是彻夜难眠的。
我希望听着堂客的“摇蓝曲”,安然入睡,直到永远。
2009--1-26(已丑年大年初一)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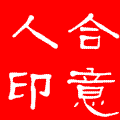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