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夯歌
那年端午刚过,我从水库工地被临时抽到右干渠的副坡上打夯。打夯要唱夯歌,夯歌唱得好,泥土也就夯得紧实,若无夯歌,任你打夯的汉子多么壮实,那夯锤落下去都没有斤两,就像拍皮球一样,轻飘飘的。
夯歌一般都是现编现唱,荤的素的都行,只要押韵。
我和建宝、贵癞子,还有陈细老官共一架夯锤。细老官年轻时放过木排,上富川、下道州地跑过许多码头,见过大世面。开始那几天,大家一致推举他唱夯歌,细老倌也 不谦让,将竹蔸烟杆往腰带上一一掖,“呸”地一声朝手收板心吐口唾沫,然后搓搓双手,弓腰抬起夯锤就唱:“放排的汉子好忧愁,日晒雨淋水中游,冷水泡饭寻常事,河风吹老少年头。:” 他唱一句,众人便“嗨嗨哟嗨嗨哟”地和一声,唱得抑扬顿挫,和声也雄浑有力,可细老倌毕竟有了年纪,中气不足,才唱几轮便奈不何了。贵癞子就喊我唱。我以前在大队办的黑板报上登过两篇狗屁文章,队里就有人喊我“秀才”,喊得我云里雾里的,于是扯起咙就唱“老后生年纪二十五,衣裳破了冇人补,有心找个补衣人,耐烦再等二十五。”
这是当年流传在江永知青中的一首歌谣,我略作改动,居然也敷衍成几句夯歌。下午歇憩时,细老倌坐在桐子树下若有所思地烧完一袋烟,忽然歪着脑壳问我今年多大了,家里订了亲没有?我一一回答后,他重新装上烟,又上上下下将我审视一番,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成份高了点,不然。。。。。。”往下的话就有些费猜了。建宝忙用手肘碰碰我,附在我耳边低声说:“你小子走桃花运了,细老倌要招你当上门女婿呢。”我耳根一热,立即就想到了细老倌那未出阁的满妹子:成份倒是绝对的过过硬,人也长得五大三粗,无论打架和做工夫都算得上一把好手,只可惜脸板上有几粒阴麻子。。。。。。”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懵里懵懂地学着细老倌的腔调冒出一句:“别的都好,只可惜脸板上有几粒阴麻子”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不想细老倌并不气恼,跟着众人一起嬉笑,笑声落后,他才挪挪垫坐的几片桐子叶凑到我面前问:“听说你们城里好捞吃,连黄泥巴和水都卖得钱,为什么还要跑到我们这里来挣工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我正不知如何回答,赤脚医生李细兰背着药箱风吹杨柳般飘过来了,大家便一窝蜂围了上去,有的要几粒仁丹,有的讨两张膏药,药箱空了,细兰妹子就坐在桐子树下看我们打夯。贵癞子将手里的半截纸烟点燃,诡譎地瞟一眼细兰妹子,然后挽挽衣袖,又将扎头裤裤头往上提一提,响喉亮嗓就开了唱:“来了个妹崽家十八九,想当新娘又怕丑,新嫁衣做了两三套,只等花轿抬起走。。。。。。”众人见细兰妹子抿着嘴偷笑,便一齐吆喝贵癞子唱下去。贵癞子嘴巴越发没遮拦,再往下,便全是荤的了。细兰妹子忍住笑,顺手抓了个土疙瘩使劲朝贵癞子扔去,正好将贵癞子头上那顶无檐烂草帽掀翻,恓恓惶惶露出一个癞痢头来,打夯的汉子更加笑得前俯后仰。。。。。。
摘自拙著《凄惶的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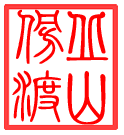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