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代初过苦日子了,那过年自然就变啦!
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在一阵砸锅毁壶炼钢铁、大挖浏阳人工河,疯灭老鼠麻雀,集体吃食堂,非常非常辛苦,又大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后,这日子却越来越苦,生活越来越差。饭都吃不饱,争吃仙泥土,糠作粑,蒿当饭,红萝卜当作营养餐。好在我得了急性肝炎,不馋饭,饥饿感觉不那么强,但也曾挖过野莱当过粮。而我最明白全家省下的粮只不过是想让患水肿病、白血病的父亲能多吃一口饭,多换营养餐。
人们自然没有多余的粮去做什么“汉茶〈旱茶〉),那炒、炸的香味闻不到,嗅不着了,我们这群半大的人也没再在一起围着灶台转,那过年的热闹荡然无痕。妈妈仍沿旧习,年前必大搞卫生,将被帐洗浆,将灰尘掸尽,没什么好吃的,但窗明几净,干干净净过年的感觉也印象深刻。
妈妈只是很难在三十晚上再为我套上新装,但妈妈仍会去银行换一叠红红绿绿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小票给我压岁,我仍是不会花它,年过了又交还于她。父亲过世,也再难见初一早上妈妈那舒心的笑,我虽然仍会轻轻地亲吻她,说上一句“妈妈:跟你拜年!”,但脸上已没有了那灿若如花。
也没有了那开财门关财门的炮竹震耳,邻居街坊仍是起早,仍会串户拜年,菜色削瘦、苍白浮肿的脸上难见喜笑颜开,只见步履沉重!而拱手时也只闻“拜个早年!”,音色失去圆润。
哎,这年年年,怎么过得象“白毛女”戏里那般沉重,难见喜色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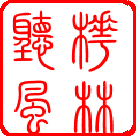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