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孟晓兄:
我现已陷入围城,等待救援。
根据淮羽兄的规定,节目时间控制在4分钟内,这篇讲稿朗诵下来有8分钟,因此要大大删减。有一些网友建议,不能将文稿改动为诗歌,要尽量保留原来的报告风格。演讲形式最适宜。
还有网友建议:不能是一人朗诵,最好是一个群体的形式。
等等。非常令人感动。
最后感谢你的帮助。
雄鸡报晓上











我现已陷入围城,等待救援。
根据淮羽兄的规定,节目时间控制在4分钟内,这篇讲稿朗诵下来有8分钟,因此要大大删减。有一些网友建议,不能将文稿改动为诗歌,要尽量保留原来的报告风格。演讲形式最适宜。
报晓兄不必犯愁,一是弟兄们不会见难不出手,况且这本是沅江知青大家的事:二是演讲本就是兄的强项,兄在沅江当着那么多沅江父母官,同去和当地的各界要人,当着挤密桠密的一台下听众尚且面无窘色,口若悬河,弄得男人唏嘘,女人落泪,现在就在咱们知青自己的联谊会上演说一遍,难不成还怯夥不成?不怕!咱怕过谁呢?
不过淮羽兄压缩时间的要求的确有些讨嫌,常识告诉我们:演讲不怕长,越长越不要讲稿,就怕短,越短越要花长时间准备,老兄,你真是遇到难题了。不过依小弟看,你还是不怕,因为你的困难就是怕没有困难,有这个挑战,你会更出彩。我看还是演讲,你适宜演讲,不适宜朗诵,无论声音条件和形象气质条件都是。wenwen姐姐的意见很有见地,咱们要好好考虑。兄意下如何?







谢谢天命兄的指教,即行送上我的认识供兄批评。
1978年2月,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嘛”。
考究一下,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好理解。国家不满意的原因考究起来至少两点,一是“社会上议论很多”,这种议论肯定是不满意,执政党不可能不关注民意。二是国家每年财政要拿出100多个亿,结果买来的还是不满意,不值。
为什么社队不满意呢,窃以为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知识青年下乡后,乡村社队的生产投入如田土、政策、财力等没有增加,农业的产量没有增加;而所承当的赋税征购指标等没有减少,结果呢,无非就是增加了吃饭的嘴巴而已。那么在两个没有增加和一个没有减少的情况之下,知识青年只有挤占农民的微薄口粮。
农民的口粮窃以为是微薄的,身在鱼米之乡照样挨饿,难得温饱。年年难度春荒。
雄鸡报晓上



报晓兄说得不错,在客观效果上,是知青“挤占农民的微薄口粮。”这点无异议。只是,农民“一把将我们1万4千弃儿揽入怀抱,让出微薄的口粮以补我们的辘辘饥肠。这般的情意叫恩德,怎敢舍弃。”这是兄的感觉,不是我的感觉,从意境上来感觉这句话,我总是希望能够找到这种温暖感觉,但是,如“弃儿揽入怀抱”那是一丁点也找不到的。当年,称为“贫下中农”现在称为“农民”的人们似乎并不需要和也不欢迎这些踌躇满志的知青们,他们基本上把这些城市孩子看成了包袱,认为是到农村来与其争食的负担。“贫下中农”们在插队的农村,各类生产建设兵团及各种农场的干部、贫协、军宣队、工宣队大都不则不扣地履行了毛交给他们的使命:将知青当作“再教育”的对象,知青们实际受到了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待遇,“贫下中农”才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当然,这是在某一种层面上的说法,在具体的下乡生涯中,某些个具体的农民与知青(如小芳什么的)有感情得到农民的帮助这种现象是有的,但那不是知青对下乡的整体感觉,如果农民真如父母一般,哪有知青现在的这么多怨恨。正如兄所说:“当年是他们,默默承受狂暴城市的撒野”,毛把矛盾往农村一甩,如果说农民在“狂暴城市的撒野”面前逆来顺受,可以认同,把“弃儿揽入怀抱,”这样说法在无意中消解转移了矛盾,也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农民、农村当时的状况。
当然,作为散文朗诵,一种文学创意,一秒就过去,咬文嚼字大无必要,只因兄回了一段,本人又见那行字有点刺眼,不由罗嗦几句。 天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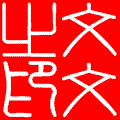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