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永的知青“闻人”
“闻人”一词最早出现在《荀子·宥坐》,“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
那书里提到被孔子砍头的少正卯是“鲁之闻人也”。把少正卯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享有“闻人”称号的第一人应该不会错。所谓闻人,愿意也是特指有名望的显达之人,是完全的褒义词。
然而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旧上海,自打出了张静江、黄金荣、杜月笙这三位“流氓大亨”,而且被冠以“上海滩闻人”的称号之后,“闻人”就变成了流氓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的代称。
我却并不认为这个时候的“闻人”变成了一个贬义的称呼,这只不过是专门用以形容他们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翻云覆雨,俨然一方诸侯的情形的。因为在旧上海,他们个人本身并没有在政、商、军、工、学任何一个部门担任任何职务,却能够对其指手划脚并施以不可小嘘的影响,就连各路军阀、政客、国明政府领袖都投靠其门下,那就还是确实具有别人所不能具备之能力。用“闻人”来表现他们的身份还是比较贴切。
而杜月笙出面把汉奸张静江杀掉,黄、杜两人始终没有为日本人做事,倒还算得上是多少有一点民族气节的。
他们也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怪胎。
论说在知青生活的“广阔天地”里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适合产生“闻人”的土壤。然而在江永的知青群里却有一位无人不知的“章某”,因其行为的特立独行、思维的诡异无常,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应该归于另类中的另类,虽然他绝对没有少正卯那样显赫的名望,也没有黄金荣等人那般“路路通”的威势,我以为就凭他那句传播甚广的名言,也可以把他算作一位“闻人”。
“在江永如果不认识我的知青,那绝对是‘野仔子’!”这是他经常骄傲地向认识或不认识的知青发布的口头宣言。
我幸而在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有缘与他见过两次,算勉强地保住了“正宗江永知青”的身份。
七十年代早期,阶级斗争的弦还是在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心中绷得最紧的时候,某一天的下午时分,他那颗硕大的脑袋上,一头油光闪亮的披肩长发向脑后梳去,成一个饭碗大小并朝外凸出的圆形,再用发卡别住,这是民间典型的、妇女同志独有的“笆笆头”;一件大花格子的衬衣将他那一身壮实的肥肉箍得绑紧的;脚下蹬一双擦得锃亮、当时少有人穿的尖头皮鞋,昂首阔步走进我们场部所在地。
他的出现,有如天外来客降临,自然引来无数内容复杂的目光,可能是他早已习惯于在众多的疑惧、警惕、不屑、窃笑……的注视下我行我素地生活,他没有丝毫的不安或局促,径直走进我的邻居屋里。
没有好久,我们在晚餐的饭桌上由邻居引荐相识了。
他坐在我的对面,左手端起酒杯,向我高高举起,右手拿起筷子先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轻轻一顿,随着说一声“乾!”两片肥厚的嘴唇浅浅地夹住酒杯的边缘,稍一吸气,“吱溜”一响之后,将空酒杯朝我一亮底,随着响亮地“叭叽”咂吧一下,然后惬意地拖长声音吐出一声“咳——”,再把酒杯放在自己的面前略微向前一推,然后夹菜,继续斟酒。
我的邻居边吃边向我介绍他的这位客人以及他的不同寻常的行为举止,“章某”——他的客人似乎并不介意叙述的过程中明显的“不尊敬”的语气。
“他是从来不出工的,”我的邻居这样说着:“只要有知青居住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一走到那里就把那里的知青的口粮吃完,然后又到下一个地方去。”
当我满脸疑惑地望他时,他用低沉的男中音满不在乎地回应我的眼光说:“是的咧!哪个会尅出工咯!”
“不过他也蛮大方,每个月公社的口粮下来,他是首先把自己的那份招呼大家吃掉,然后才出去呷!”我的邻居还是怕伤害他的自尊,“他屋里把他的钱他也拿出来大家花!”为了佐证“有钱大家花”的可靠性,邻居又补充说:“他牙娘都是高干,屋里有钱!”
“那就不呐!”这句话遭到“章某”激烈的反对,“他们把钱把我,那还要看我的心情好不!”他一脸不屑的表情,“即算要接他们的钱,我也要转过背,反手去接!”他流露出来没有丝毫做作的那种明显的鄙夷的口气使我大为惊讶。
按照“章某”行事的原则,他是要在我的邻居那里留宿的,但是这里的保卫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警觉性不是一般的高,晚饭后不久,就有人来下“逐客令”,不允许怪异的“章某”在这里住宿。没有办法,那个年代公民的自主权实际有限得很。他悻悻然离开,去了小河那一边的管家大队。
时隔不久,又有了第二次见面。因为已经认识,他又是一个不分亲疏的人,只要有人招呼,就自然和他熟络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把油亮的齐肩长发梳成“笆笆头”,而是让它们像瀑布似的飘洒在短粗的脖子以下,像一头非洲荒原上气定神闲的雄狮。
“你的头发就有蛮长呐!”随便聊过几句闲话之后,我想解开心里对长发的迷惑,便这样开始问话:“不大方便噻。”
“那不觉得咧!我从小就蓄起。”他很不在乎又有点自豪地叙说道:“有一回被县里民兵指挥部的碰见,硬押着去理发店,要剪掉我的头发,我又犟不过,只好被他们按哒坐上去,”他喝了一口茶,夹在手指间的烟在袅袅燃烧,接着又说下去:“等那两个民兵一松手,剃头师傅的剪刀才一放得我脑壳高头,我就大喊一声‘哎哟咧!剪不得哒、剪不得哒!’,跳起来就跑。”我大笑不已,心想这家伙还真的有味。
“未必你连冒碰见过麻烦?”我的意思是,就凭你这副模样,在这到处都是警惕着阶级敌人的年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革命群众”的注意的。
“那禾式冒得咧!”他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慢慢的吐出,饶有兴味地说:“有一年回长沙,我坐在冷水滩车站的候车室里一边等车一边打瞌睡,晓得有两个民兵在我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反复打量我,想问又不好问得一样,怕莫以为我是什么华侨之类,我也不理他们。”
这时候,他自己也陷入得意的回忆当中,脸上露出那种藐视一切的笑容,继续说下去“他们还是忍不住疑惑,把我摇醒后问我:‘你有车票吗?’我从口袋里掏出车票递过去,话都懒讲得。他们又问我,‘有证明没有?’我又到口袋里掏,半天才摸出一张纸来,交把他们看,那是一张公社里开的要我到队上出五十斤谷的条子!”那两个要查看证明的民兵这时才明白,自己要搞清来历的这个人,只不过是一名没地位,没“身份”的知青,“章某”也觉得他们应该是受到了自己的捉弄,说完之后,他首先笑起来。
若干年之后,“章某”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回到了长沙,开始重新找回失去的自我,却听说他并不适意。
曾经听他说过自己有四个第一。
唱歌,“世界上不该出了一个帕瓦罗蒂,除了他之外……”他没有说下去,但言下之意已经明确无误的说明,自己应该与之在伯仲之间;
书法,“狂草不如怀素、小楷不如曦之,这是不争的,除此之外……”他也没有继续说下去,不难想象,此刻他内心恐怕也产生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概叹;
写作,“讲明的,我是不动笔,只要一动,‘渃贝尔文学奖’就要落户中国!”他这样宣告自己的凌云志向;
哲学,“‘笛卡尔’、‘卢梭’……哼!可惜不能和他们同堂辩论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由衷地表现来出万般的无奈。
就是这样一个傲气十足的“章某”,却对广生哥佩服得到了几近崇拜的地步。
那是在他父母搬出位于水絮塘市传染病医院旧宿舍以后,因他不愿随父母移住新居,就一个人享受这一套房子,乐得一个自在。谁知没过多久,单位要索回这套宿舍另行分配给他人,限令他于某日搬出去。情急之下,他找广生哥为他出主意。
“禾得了咧,”他一脸焦灼万分的表情,让广生哥怦然心动,“他们明天就要我搬出去呆!我又住得哪里尅咯?”
“你先莫急咯,”广生哥安慰他说“总会有办法的,你让我想一下。”
“章某”开始抽烟,大口大口地把烟吐出来,仿佛要在缭绕的烟雾中找到对付母亲单位要他搬家的对策。
“你看是呙样的要得啵,”在抽掉两根烟之后,广生哥讲出他因人制宜想出的办法:“你要在他们敲你房门的那一瞬间,猛地拉开房门,左手半握拳,向胸前弯曲,右手也半握拳,手臂向身后伸直,左脚向前迈出一大步,右脚向身后绷直,左脚膝关节稍弯,成弓步,头部要高高抬起,眼睛尽量瞪圆,一声不吭地看着来人。”广生哥一口气连带比划做动作,讲完这个主意,望了一眼满脸愕然的章某,略微有点犹豫地再补充说:“这是第一招,如果这一手拿出来还不管用罗,那就只好用绝杀招哒!”
“还有么子绝招罗?”章某急忙问道:“快点讲噻!”此时此刻,广生哥就是他心中的上帝。
“那就是该样的,”广生哥望了一眼渴望得到锦囊妙计的章某,“你就只有把头再抬高些,尽你最大的底气,对来人大吼一声”,看到他还在等待下文,广生哥只好把话说完“这一招拿出来还没有用,那我也冒得办法哒。”
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下午时分,“章某”兴冲冲走进广生哥的超市里,大笑着告诉他,“你那个办法真的灵!我第一招还冒完全用出来,那几匝鳖转背就屁滚尿流的跑噶哒!”事后据说还有一个跑得太急,把脚脖子给扭伤了,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康复。
自此,“集当今数一的‘歌唱家、书法大师、渃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哲学家’桂冠”于一身的“章某”对广生哥是鼎力赞扬不已:“那是一个真角色”!
“章某”能不能称为“闻人”并不重要,也不是我要说的主题,我也绝无轻视他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的生活,“章某”也不能例外,尽管在我看来他并不那么遂心如愿,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苍凉凄婉。每一想起知青中的各类风云人物时,总觉得无论是辉煌或是平庸,都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烙印,逃避不了的。
毫无疑问,人生就是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一样,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复杂内容交替出现的漫长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便有不同的主题。知青阶层的出现不也就是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的历史的一个进程么。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曾经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原始的传统、远古的神话、中古世纪的宗教、近代的文学和现代的科技。这些遗产都同样的灿烂夺目,照耀人类的幼年、童年、少年和成年,它们装点并充实了各个不同的时代,甚至过去了几千年还令我们神往。但是,如果我们颠倒了它们,比如在今天还去编织原始时代的神话或中世纪的颂神诗,那就显得荒唐可笑了。
唐·吉柯德毕竟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不必当真。人,不能生活在虚无缥缈的幻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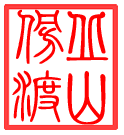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