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 行 记
小时候听人讲鬼故事,我夜里就做恶梦。长大后我身体特别文弱,况且母亲以前请的算命先生又说过:我“火焰低,不宜夜行”。于是,我在下放农村前从未单独走过夜路,但是20世纪70年代我落户在常德桃源乡下时,却麻着胆子,一个人走过一截几十里远的夜路,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那次夜行是在落户后的次年,端午节那天上午,我从省城搭一亲戚便车到了常德市,下车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而当时去我的下放地桃源杨溪桥方向的长途汽车票已售至第三天,而我身上又没带多余的食宿费,可以在常德城里留宿一夜。(我原以为在常德下车就可以打到下午去落户地的票), “人太紧则无智”,我一看天色越来越晚,心里像有蚂蚁在扎一样难受,急得更慌了。如果是在上午,还可以在公路边去求货车司机,可下午四、五点钟去湘西方向的货车已经寥寥无几了。思来想去,最后我想到的是一个最差劲的笨办法:傍晚开始走路,到天亮时去拦搭我身后从常德出发而来的早班车。
打定这个“馊主意”后,我又揣度着:自己不能走得太早,太早了我的双腿走不了一通夜那么久的路,怎么能熬到天亮时分呢?于是,我就提着行李袋沿着常德街头徘徊……前后足足踟蹰了一、两个钟头,捱到天黑我才背着行李袋,沿着向湘西方向的公路步行返队。
离开常德汽车站,走了约半个钟头,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感到肚子“咕哝、咕哝”叫起来了,便在路边一块凸起的大石头上坐下来,拿出身上仅有的一个干法饼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到剩下半个时我就没敢再往下吃了,而将那半个留存袋中,好等途中饥饿时“敷衍”肠胃一下。我站起复继续赶路,一会儿头顶现出了些许惨淡的月光,我仿佛瞧见了前面不远处的村落,人的本能中害怕孤僻、渴望“合群”的心理驱使我加快了脚步……我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自己走了多远?惟见月亮已悄悄爬上了半天空。我抬头专注地凝望着月儿,只觉得夜空的月光特别苍白,特别冷清,特别失色!全无平日夜中月光带给人的那份恬静温情,更谈不上外国经典《月光曲》中的诗意了!月光无声地笼罩着四周茂密的山野和空旷的田地,在静得出奇的夜色中,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地直跳,这是幽黑的夜色和惨白的月光带给我的恐慌,我暗暗给自己打气:鼓足勇气;同时叮咛自己:尽量不去想象孩童时代所听到的那些吓人的鬼怪故事。
就在我走得非常疲惫、忐忑不安的时候,从我的身后方忽然传来了一部长胶轮板车“嘎吱、嘎吱……”的车轮声。人的出现及车轮的响声打破了万籁无声夜幕下的可怖,我孤寂的心灵终于安宁下来。可能是条件反射的原因,走了数十里远的双腿这时终于不听我使唤了,我便在路旁停歇下来,退而坐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小歇,边歇息边等走近的车。十几分钟后,拖着一部长板车的老伯在我的目光中越走越近了,当他经过我面前时,才发现路边树影下呆坐在石块上的我,未料到深夜路边会坐人的他,吓得突然发出一声厉问:“干什么的?”
我忙上前笑了笑,接着回答:“大伯,俺是赶夜路的知青。”
当他知道我是下放知青,要急着赶回生产队,才去掉戒心。然后,他友好地要我坐上他的车,载着我朝前行,我庆幸半夜遇上了好人。走了约莫八、九里路,老伯在公路旁一栋小屋前停下,对我说:这就是他的家,要我跟他崽睡。早已筋疲力尽的我巴不得马上躺下来,任何问题都没想就跟着他进了屋,随即我泥手泥脚摸黑爬到了他崽身边,挨着打着呼噜的老伯崽睡下了。刚躺下,破帐内外的蚊子“嗡、嗡、嗡”围着我直叫,我在它们的“夹攻”下无法入睡,轻轻地翻了几个身还是没完全睡落觉,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寤寐之中,直到天微微亮时我才勉强迷糊入了睡,梦中忽然又觉得周身有小虫在咬,发起痒来,一发而不可止住。我开始以为是蚊子叮咬引起的,痒醒后我用手指狠戳痒处,还是止不住那种奇痒,直搅得我在床上翻来覆去……
但奇怪的是:老伯的崽却酣睡得如同死猪一般,毫无反应。捱呀!捱呀!终于捱到窗口透进了一线白亮的曙光,我如同得到“大赦”的罪人,立即爬起床,老伯也进来叫醒了崽。我这时才仔细端详了一下坐在床边的老伯崽:他头上竟白一块、黑一快,脑袋及全身手足到处又是一团团的模糊红斑块,我一下惊愕了!他这身红、黑、白混杂的斑痕莫不是当地流传最广、最难治的皮肤病——“铜钱癣”吗(我们生产队长两兄弟就是这样的癣患者)?那一瞬间我感到双腿在颤,浑身上下爬满了鸡皮疙瘩。
正在犯怵的我,突然听到老伯问:“小伢,吃完早饭再走。”
我早已心乱如麻,那还有心思吃得下这顿饭?即刻起身辞谢!
那个苍白的月夜使我至今难忘;那位善良的老伯使我至今怀念;那身可怕的癣斑使我至今后怕。从那时到现在,我对皮肤发痒仍然特别敏感:每当皮肤出现一丝红斑就会神经质般过敏;每想起老伯儿子那身令人不寒而栗的“铜钱癣”,全身就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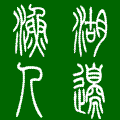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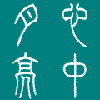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