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这个巨大而突出的问号渐渐占据了郝大江的大脑空间。
作为一名头脑冷静勤于思索的十八岁的“老兵”(北京老红卫兵自称),郝大江,这个出身高干家庭的北京六十五中高才生开始苦苦思考上述意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当时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刚刚形成燎原之势,伟大领袖神采奕奕八次接见红卫兵,将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向全国城乡。而北京红卫兵的斗争锋芒已经从“破四旧”转向打倒走资派,昔日高高在上的人民公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丑八怪,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
最早被鼓动造反的干部子女和老兵们顿时陷入窘境。他们自以为出身优越,精神高贵,血管里流着无产阶级鲜红的血液。他们造反是为了造别人包括一切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的反,不料这股由他们掀起的革命浪潮却冲进自己家里,革命革到父母头上,这个难以承受的现实使他们又难堪又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优越感一夜之间一落千丈:出身不再优越,血统不再高贵,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红色而是别的什么颜色的血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岂料龙种凤胎也有钻地洞的时候,而且钻得更狼狈,更连老鼠也不如,这就很有些伟大领袖教导过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讽刺意味。
或疯狂,或绝望,或堕落,或沉沦,或一蹶不振,或举止反常。也许人类只有设身处地经过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才会懂得世界需要同情,需要爱。
也有苦苦思考和求索。
对北京六十五中早熟的红卫兵领袖郝大江来说,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思考的前提乃是怀疑,对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运动方向乃至领袖权威产生怀疑直至否定,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量和勇气。
公正地说,公元一九六六年的郝大江们不具有这样的力量和品格。
历史的局限将束缚一切人,也束缚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伟人。郝大江们只是由于家庭受到冲击,由于自身价值的失落才产生与运动对立的消极情绪,他们并不想向运动挑战,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叛逆。这样,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依然是优越的,居高临下的,而浓重的怀旧情绪又注定使他们的目光无法超越自身和穿透重重的历史迷雾。
但是思考毕竟不同于盲从。
思考能够使人冷静,使人在随波逐流的年代摆脱盲从的惯性,部分或全部恢复人的理性本能,从而有可能作出比其他人更接近真实而不是虚幻的独立选择。
在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选之后,十八岁的红卫兵郝大江和他的战友终于从领袖教导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顺着领袖的思路并不困难地找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不是以经济而是以政治为目的)重新维护和证明自身的阶级忠诚和优越感。
西双版纳之行大大激发了红卫兵们的热情和愿望。十二月中旬,一个类似招兵站那样的联络机构在北京东单金鱼胡同宣告成立。联络站是民间机构,不挂招牌,由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为保密起见,互相用代号联系,于是就很有些地下组织的神秘味道。在当时派系林立和造反组织多如牛毛的北京,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许多伟大和不够伟大的人物都站在同一个时代舞台上竞相表演,成为来去匆匆如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总之竟没有人注意东单路上那条僻静的金鱼胡同和胡同里一群忙忙碌碌的中学生的存在。
社会的疏忽造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之梦。
联络站一经成立,报名者竟然十分踊跃,当然并不排除多数报名者并非出于理想而是因为好奇,或者对运动的悲观厌世,但是同盟者的猛增毕竟大大鼓舞了年轻的组织者。五人小组参照电影里那些地下党的工作模式,对前来报名的同龄人进行单独谈话,严格政审和考察。首要条件是出身,因为理想是纯洁的,所以出身必须纯洁无瑕。出身按照阶级顺序依次排列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优先,工人、贫农次之,其他劳动阶级再次。知识分子与九种人并列,属于反动分子。政审结果,共有数百名红卫兵被光荣批准加入拓荒者的战斗队伍。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失意的干部子女,也有少数工人后代,他们都为自己的光荣出身和阶级使命而自豪。
为进一步坚定信心锤炼意志,他们将队伍分批拉到京郊门头沟煤矿进行长达数月的劳动锻炼,与矿工同吃同住同下井,不搞特殊化,还常常进行野营拉练和急行军。总之他们随时随地想到自己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正担在他们肩上,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正等待他们去解放,任重道远,因此他们每个人都不甘落后,把这些演习和拉练做得很努力很认真。他们给自己的计划起了个极豪迈的名称,叫做“开拓号工程”。
不幸的是,“开拓号工程”由于形势的原因搁浅将近一年。
当一九六七年深秋呼啸而来的寒风将首都大街上的黄尘和翻卷的大字报一起刮到天上去的时候,全国性武斗和造反派夺权正进入如火如荼和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
国家经济好像一条机器熄火失去动力的破船,在政治风暴的滔天大浪中随波逐流,随时都有倾覆沉没的危险。
十一月,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频繁接见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代表,传达毛主席一项又一项最新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要斗私批修。”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
二十七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领导人在东北厅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传达最新指示:
“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要复课闹革命。”
尽管红卫兵小将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为什么犯错误也要排班站队的深刻道理,但是有机会聆听领袖指示和领导人声音还是使他们激动万分。
接见持续到凌晨一点。
其间,周恩来一度感到不适,小腹坠胀,并伴有轻微压迫感。虽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几年后将吞噬他生命的膀胱癌细胞在作祟,他还是决定起身离去一会儿。
对于台下的普通红卫兵来说,领袖和伟人的一举一动有时都直接关系他们的命运。密切注视总理动向的郝大江感到一阵心跳。为了找到单独接近总理的机会,他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好几个月。现在他知道,机会到来了。
郝大江在衣袋里摸索了一阵,匆忙中他发现自己竟然忘记带本子,因此只好向邻座讨了一只空烟盒。他掏出钢笔在烟盒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用目光示意同伴跟他离开会场。
十几分钟后,当周总理疲倦的身影从大会堂厕所里走出来的时候,四名穿黄军装的男女红卫兵突然从楼道一侧钻出来拦住他。
“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请总理批准吧。”红卫兵七嘴八舌地说。
总理没有思想准备。在他的工作日程里,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都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事,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他只是喃喃地语重心长地对小将说:
“就要复课哩。你们要复课闹革命哩。”
小将们急了,连忙声明:
“我们都是北京的应届生,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报告。”
日理万机积劳成疾的总理终于有些明白,眼前这些生气勃勃的红卫兵与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的红卫兵小将不大一样。他们不是来斗争谁,或者告谁的状,或者领了某某一纸批语就回去当做上方宝剑压制另一方,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这些年轻人站在他面前,眼巴巴地望着他,请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从事艰苦的经济建设而不是阶级斗争,这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倡导的好事呀!
后来人们回忆,当时总理接过报告,眼眶稍许有些潮湿,还有人证明总理喉咙里曾经发出一声轻微叹息。
所谓报告,不过是一张画满字迹的烟盒纸,并且字迹匆忙潦草。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在去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西双版纳进行调查、联系,深切了解云南边疆很有开发前途,尤其是那里有发展橡胶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请总理下令吧!”
署名是“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
总理把字条接连看了两遍。这就是说,这群年轻人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早有准备并做了大量工作。如果全国的红卫兵都像他们这样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从空洞的口号出发,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船不是可以稍稍减轻一些负载而增加一点动力吗?
大会堂内的嘈杂不容许周总理的思路继续深入下去,他将字条仔细揣进衣兜里,匆匆做了一个手势说:
“好好,我看看再说。”
纸条和希望一同被带走了,联络站的郝大江们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一整夜。在路线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也许到边疆并不是大方向,也许周总理对他们的胡思乱想不感兴趣。他们应当同别的红卫兵小将一样,回到学校去复课闹革命,参加上层建筑斗批改。也许他们的举动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那样:“现在轮到……犯错误了。”
总之光明与黑暗并存,希望与失望并存,苦恼与信心并存。
第二天上午,总理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传达总理批示如下:
“可考虑这个请求,请与北京市委联系。周恩来。”
总理指示被迅速贯彻落实。中央传阅文件1967(67、70号),第一张原始附件就是出自郝大江手笔的那份不伦不类的报告。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我们很难断定,这群热血沸腾的中学生的激情和冲动究竟是否给周恩来,给中南海以及当时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留下过什么印记,或者提供某种思路?而这份中发文件的影响与一年之后传遍中国大地的那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只有一点确凿无误,那就是“文革”期间以中央文件形式单独批准上山下乡的仅此一例,而这一小批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无疑将成为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并因此载入历史。
不到一个月,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障碍扫除,一切关卡放行。从西双版纳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等待郝大江们的将是一片充满绿色希望的广阔天地,一条洒满金色阳光并且越走越宽广的康庄大道。
知识青年将在那里大有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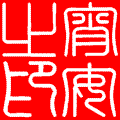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