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草鞋
因为记挂着亲人和朋友,昨日离开温暖的海南回到长沙。甫一归家,见到冰封雪盖、银装素裹的景色,十分欣喜,总算赶上了寒冬的尾巴,欣赏了多年不见的冬景。然而,欣喜之情很快就被种种不便冲淡。地冻天寒,时不时停电,自来水供应也不正常,空调、烤火炉、热水器全成了摆设,屋子里冷冰冰的象个冰窟。穿着棉衣棉鞋全副武装地坐在家里仍然冷得发抖。出去溜达一番吧?刚出门,“刺溜——”,走在前面的小伙子在结冰的路面上一下子溜出去好远。俺这老骨头可不敢试验,折回来,找床烤火被盖着腿,望着窗外发呆。天地一片寂寥,池塘上也结了冰壳,繁忙的街道上难得见到行人和车辆,平时喧闹的麻雀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不是有句老话“麻雀也有个三十夜”吗,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了,它们大概也找个角落,妻子团圆去了。思绪悠悠地便想起了知青岁月,想起了草鞋,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双草鞋就不怕滑了”。
下乡的头一个冬天也是这么冷,可是集体工还是要出的,除了修水利,多半是割茶垅,将油茶树林里丛生的荆棘和杂草砍掉,堆起来放火烧成草木灰,撒到茶树篼子下做肥料。杂草上结着冰渣子,像刀一样锋利,荆棘毫不留情地扎进手掌手背,手冻僵了,扎着刺、流着血也不知道疼痛。下雪还好,雪是轻柔的、蓬松的、软软的,哪怕落满了满头满身,扑打抖落一阵就没事了,最要命的是冰冻。湘西有句谚语:“脚冷天色手冷晴,屁股冷了要下牛皮凌”,牛皮凌就是冻雨。贮满水的冬水田都冻得硬邦邦的,屋顶上、山坡上、路面上到处蒙上了一层凌毛子,路便象涂了油一般的湿滑,尤其是石板路,像镜子一般放着光。我下乡时带的唯一的一双解放鞋鞋底早就磨得光光的,因此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常常是刚刚爬起来又扑哧一声摔下去,惹来许多并无恶意的哄笑。只有住户老舅心疼我,不声不响地搓了两根草绳,缠在我的鞋子上,这一来强多了,靠这个办法,以后就很少摔交了。
于是第二年便学了乖,从秋天开始就拜老舅为师学打草鞋。先要从山上选那长得又粗壮又结实的“黄子”(一种山芦苇的穗杆),采回来一把把扎好挂起来晒干,准备做草鞋的筋索。那个季节,我们屋场前面的坪场便成了一片金黄色的海洋,老舅背着手在一行行的“黄子”中间踱来踱去,不时动手剔去他不满意的对象,那神气就像一位统帅在检阅着他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打草鞋的稻草也要挑选结实坚韧、色泽金黄的,不符合条件决不将就。老舅挑选材料的眼光就像他挑女婿一样的挑剔,即使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黄子”和稻草,最后真正能用上的也不会到一半。
收工回来,吃过晚饭逮一口草烟,燃起枞膏照明,就要开始学艺了。火坑边摆着草鞋板凳,那是一种矮矮的、前高后低、高的一头有两个木桩、专门用来打草鞋的四腿长凳,但老舅不爱用,他说用板凳不得力。他习惯坐在火坑边的地板上伸直了腿脚,把打草鞋的钩几栓在腰上,用木棒槌把晒干的“黄子”捶柔软了,搓成细细的结实的筋索,穿挽成四股筋,一头栓在腰间的钩几上,一头穿在两根草鞋棍上,然后把草鞋棍夹在赤裸着的脚趾上,再顺手拣上好的稻草编织起来。这时候的老舅好象换了一个人,眼里放着光彩,手脚的配合格外灵活,口里念叨着:“筋索要紧,续草要匀,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该收要收,该放要放。”那架势就是在打造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一件艺术品。笨手笨脚的我,忙乎了好几个夜晚,编出来的草鞋不是长得像条泥鳅就是圆得像只团鱼,分不出左右,更配不成对,都被老舅扔进了火坑。只到有一天,老舅审视了老半天,叭了一口烟说:“马马虎虎自己穿吧,不要说是跟我学的,惹人笑话。”那个冬天我穿上了自己打的草鞋,惹得爱说笑的妇女和半大孩子编出了一句口白:“知识青年下乡来,机器袜子套草鞋”。说笑归说笑,穿上草鞋,出工、打柴、赶集都利索了不少,因为草鞋,我和乡亲们的感情因此更贴近了不少。
时光一晃过去快四十年了,看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草鞋,想起了火坑中跳动的火苗,想起了教我编草鞋的老舅。人老容易怀旧,我们怎能不怀念那已远远逝去的苦涩的青春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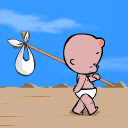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