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难忘的旅途
这几年,出差坐过火车的人都清楚,沿途大、小车站都挤满乘车的旅客,上车的人多,下车的人少,外出务工的人流,不分季节,向南方涌动,只见潮涨,不见潮落。趟趟列车人满为患,列车上送盒饭,送开水和卖小食品的服务车通过都非常艰难。旅客像一根根筷子插进了竹筷筒中,动弹不得。行旅架上堆满了编织袋和塑料薄膜包裹着的被褥和衣物,又占驻了车厢内的有限空间,车内的空气无法流通,被压缩得更加浑浊,呛人的气味,乌烟瘴气,熏得旅客睁不开眼睛,令人窒息。单薄的京广线承担着铁路沿线几亿人口的运输任务,早已不堪重负了。
我回家拿了换季衣物,又要回牯背岭。实在不愿去为买张车票,耽误半天的时间。托熟人买火车票,不好过分要求买自己适合的那趟车,只要不用自己排队,有张车票就行了。
火车下午五点开的过路车,我四点钟就得吃晚饭,腹中残存的食物未消化掉,还吃不下东西,考虑到坐火车,不确定因素太多,还要吃塞东西放进肚子里垫底。
我匆忙赶到车站。车站到处都是外出谋生的人,他们背着大包小袋,集中到火车站川流不息。我随着人流挤进了车站。今天,车上没下来几位旅客,仍是满满的。上车的人太多,争先恐后塞在车厢门口,谁也挤不进去了。眼看到了发车时间,站在车门边穿铁路制服的女人着急了,敞开喉咙叫喊着:“还有人没上车,快往车厢中间走,别堵在走道上。喂!门口那位别楞着,往里挤呀!”她指着位堵在门边,还未挤进去的女士,又大声喊:“喂!”挤在门外的几个人同时回头望着穿铁路制服的女人:“说你们几位。还犹豫什么,又不是上花轿,克服点困难,别堵在门口,使点劲往里挤!”人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车,误了不少时间,车注定要晚点了。我夹在人群中,心里只犯嘀咕,还不知道下几站还有多少人要挤上这趟列车。
我将挎包挂在胸前,颠着脚后跟,自己根本不用使劲,随着拥挤的人群慢慢地挪动。这招,还是在革命大串联时学来的。用这种办法,免费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没挤伤,鞋没被踩掉,挎包也没挤破。我没想不到这办法,又派上了用场,还蛮得意的。
我随人流挪到车厢的洗漱间。这儿早有八、九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正蜷缩在洗漱间里面。看样子他们实在太疲惫了,东倒西歪,相互依偎,或靠,或趴在编织袋上酣睡,像上辈子就欠睡,正好抓住这难得机会找补回来。他们身边挤满了旅客,懒得抬一下眼皮,甚至可以不吃不喝,省去了尿尿,拉屎,不到达目的地前,他们是不会动弹的。待车到终点站后,他们立刻精神抖擞,想尽办法,找活干,盼赚点辛苦钱,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子女上学交学费,为了救治亲人支付医疗费,对车上发生的事,用不着去操心。
我根本无法插进他们的领地,只能保持金鸡独立的姿势。没办法,只好又拼命朝前挪。好不容易挤到乘务员休息室门口,这里能勉强插进双脚,还有股嗖嗖的凉风,才觉得喘气舒畅了点。心里一乐,车上再去哪儿找这样的好地方!我在这儿休息会,先把这身臭汗吹干,一会儿,汗吹干了,身上却留下一层薄薄的盐霜,粘在身上很难受。我好喝水,车上没水喝,要强忍着。我奢望:有盆温热水抹澡,有杯热茶喝就美了。
休息室内坐着位年轻的乘务员,他的职责是为旅客服务,却无法迈出这个门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没书看,二不读报,两眼望着窗外,傻样地坐着,显得很无聊。我见里面还可以容纳下两个人。我寻思着:能混进去坐坐,喘口气。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唯一的办法是能够与他交谈,才能寻找到机会。
我没话找话,主动与之搭讪。那年轻的乘务员对我根本不理不采。我脸皮厚,见他的表情并不讨厌我,估计会有点希望。我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机会,用热脸去贴他的冷脸,厚着脸皮再去试试。我从口袋里拿出盒自己都舍不得抽的香烟,打开抽出支恭恭敬敬地递给他:“请抽支烟。”开始年轻人根本没打算接。我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学着样板戏《沙家滨》阿庆嫂那诙谐的口吻对他讲:“来!烟不好!请抽一支!”这办法还真灵。他抬起头正眼望了望我,这办法仿佛对他有点促动。他又用极快的目光顾眄烟盒,看清楚了,这烟是本地的一种高挡烟,又瞅了我一眼,不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外出谋生的打工仔。至少算是个“破落白领阶层吧”。他这才用正常人应有的目光再朝我望了一望,接过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从鼻孔慢慢地冒出烟来。我的想法,他心知肚明,看他这驾式,并不想让我进去坐,很让我失望。我心里也清楚,他接过我的烟和让我进去坐,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他没有必要对我兑现没有任何承诺,仍旧可以悠然自得地望着窗外,让凉风吹拂着自己。
我挤在窄小的空间不能动弹,等待着,希望他发善心,让我进去坐,觉得时钟间走得越来越慢。手表的秒针在嘀嘀哒哒地走,每秒的时光并没拉长,可每分钟却有八十秒,难说清楚,可能还会更长些,我渐渐失去了信心。暗暗在责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用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太不值。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车厢的灯全都打开了,广播里在一个劲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平时最爱听这首歌,今天越听越烦,什么生活比蜜甜,老子比黄连还苦。
也许他是一个人坐在那儿觉得太枯燥乏味,或是有其它什么原因。他用施舍者的口吻,说:“喂!你进来坐。”我不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愣住了。年轻人用手指了指椅子:“哎!你进来,坐。”尽管他脸部并没有什么表情,但这回相信是真事了。我喜出望外,连忙拖着麻木的双脚,挪了进去。我顿时感觉到全身被挤压的筋骨舒展开来,嗡嗡作响的脑袋也慢慢的清醒了,有座位的滋味真好。再听广播里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又回到了以前的感觉,真还有点比蜜还甜的味道。
为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或是为了感谢这位年龄至少小一轮的年轻的人,或为了讨好他,也可能是三者兼备。待我有了精神后,就马上发挥自己能侃的特长,天南地北奇文轶事涛涛不绝胡诌起来。年轻的乘务员被我的讲话深深吸引,听得津津有味。门外的人也在静静的听着,窗外习习凉风扑面而来,我很惬意,门外的人羡慕不已。
列车的钢轮在铁轨上不知疲倦地滚动着,发出均匀的哐当、哐当的声响。我好像跨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理想的世界,一切都觉得美好,再仔细看看这位年轻人,觉得他长得挺帅,想夸他象那个影视明星。但是,近几年影视届的宣传铺天盖地,阴盛阳衰,宣传女明星远远超过了对男明星宣传的力度。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位男明星与谁相像,不好用这种方式去恭维他,搜索枯肠,准备改用其它的话题。
过不了多久,有个广东口音的小伙子,对着乘务员说:“先生,请出来一下啦,有戏(事)找你啦。”乘务员比猴还精,知道在他的话语中在暗示着什么,立即使劲挤了出去。
我凭第六或第七感觉到了危机感,好景不长,这儿要换人了。我用警觉地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俩一眼。见那个广东口音的小伙子,尖面猴腮的,穿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其气质与这套高挡运动衣毫不相关,无法掩盖他那猥琐的模样。我越看越像个吸白粉者。他拿出两包“三·五”牌香烟,做贼似的塞给了乘务员。乘务员挺专业的接过香烟,用极麻利的动作揣进了口袋。年轻的乘务员讨好神色地对那小伙子耳语了几句。尖面猴腮的小伙子笑而点头作答。他转背进来,脸上好不容易才有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带着几分愠色,对着我说:“出去!”声音不大,态度很坚决。我再看看年轻的乘务员,筒直不敢相信,他怎么长得与那个小伙子一个模样,真象孪生兄弟。我心里在暗暗地骂着,丑八怪,真难看,还想象那位明星,你也配做明星,做梦去吧!我心里仿佛好受多了,知趣,不得不灰溜溜地从刚刚坐热的凳子上站了起来,又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看刚刚坐热的地方,平静地挤出到门外。
这时,我像阿Q受到赵老太爷呵斥,不再承认我是“革命党”了的感觉。讲粤语的小伙子横了起来,像位凯旋归来的将军,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坐在滚烫的凳子上,又与年轻的乘务员和谐地谈笑起来。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各种人因所站的角度不同,按“经济规律”办事,采取的不同的手段,他的做法也不一定出于本意,只不过在利益的权衡下,他宁肯舍弃我,不能去责怪年轻人。况且,我与之萍水相逢,已让坐了会儿,优惠过。有些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至上的关系,连女人的肉体都可以用来交换金钱,有买家就有卖家,什么事都可以用金钱去获取,这样的遭遇就见怪不怪了,人要知足,算是有滴水之恩吧?
我又挤在原来站的地方,时刻有人想尝尝凉风扑面而来滋味,朝这儿挤。我从小就干过苦力活,人也长得敦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捍卫所站立的这块“领地”, 不是别人想来夺就能轻而易举夺走的。自我感觉好了,人不能事事与人去较劲,要有点阿Q精神,过得去就该知足。
我又清晰地听到,列车在不知疲倦地滚动,依旧发出均匀的哐当、哐当的声响……
我的脚被挤得没法挪动,随着时光缓缓地流逝,脚渐渐麻木到肿胀,又慢慢地失去了知觉。火车像位七老八十的小脚老太太,还那样按部就班,不急不慢地走,根本顾不上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似的旅客。他们希望早早结束这次难熬的旅行。列车每经过一站,就要晚点,累积起来,到达白石渡车站,整整晚点两个小时。对铁路部门来讲,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了,旅客都理解。我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脚下火车,一个趔趄踏空了,差点摔倒,我赶紧抓住车厢扶手,站稳,缓缓地活动筋骨,才能慢慢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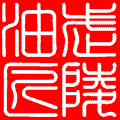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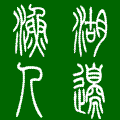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