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七)小店轶事
食堂的早饭开过了,只好去牯背岭对面的小店吃碗米粉。我来到小店,又换了个新老板,他们卖了一早上的米粉,正坐在矮板凳上摘菜,准备中餐。他们不认识我,见有人进来,爱理不理。我看到灶边的案板上,放着个笠箕,里面还有些碎米粉,勉强凑起一碗的米粉。米粉搁在这经风一吹全干巴了,像随手扔在基建工地一堆生锈的扎丝。可自己还是昨天上车前在家里吃过饭,都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饿极了。离开午饭还有几个小时,米粉碎点没关系,能填饱肚子就行了。我要了碗肉末粉(这儿离广东近,生活习俗与他们类似,肉末粉是用生肉末在米粉汤中烫熟。)。老板打算将这点碎米粉倒入潲水缸去喂猪。见还能卖几个钱,求之不得。老板马上叫出在内屋清理营业款的老板娘赶紧出来下粉。
老板娘将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上了桌,上面没有一丁点肉末,仅有点些干瘪皱巴巴的花生米。我问了句:“怎么没肉末?”老板娘一翻白眼:“肉末没有,放花生米比肉末要香,好吃。”
我是所谓省里来的人,在郴楠乡在人们眼中好歹是个公众人物,自己得装出文雅大度的模样,不能讲半句使人生厌的话语,这样虽然活得特累人,却没有办法。我看到这些干瘪的花生米,只能在脑海中翻腾,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在昨天夜里,几个喝酒的朋友凑在一块来小店宵夜,几盅白酒下肚,血管臌胀,满面红光,阔论高谈,声浪一个盖过一个。拼盘和几个炒菜吃完,剩下这盘油炸花生米,他们用筷子轮番把这盘花生米扒过来拔过去地选,“矮子”中间挑“高个”,觉得能看上眼的全都嚼碎吞吃下了肚。剩下的这些难看的残次品,没被他们选中,经过唾沫沐浴,全被丢弃在桌上。夜深了,客人走了,老板劳累了一整天,困了,眼皮重千斤怎么也睁不开了,也就懒得去收拾,只想早早上床睡觉,他伸了个懒腰上床便呼呼睡着了。
老板开店以来,天天都盼生意好。可是,在这地方开店,人们消费者观念不同,抠到的几个钱,看得太重,舍不得花。老板想尽了各种着数,招揽顾客,人累得像旱天的禾苗,头也抬不起来,还是赚不了几个钱。俩口子好久未亲热了,夜里女人总是推自己的男人,想干点什么。可是她老公要死不活的样子,沾床就呼呼大睡,连话也懒得说,把这事早忘到霄云外去了。他也不知道又有多少日子没碰过自己的女人了。现在,外面的诱惑太多,防不胜防,要不是两口子行影不离,她真怀疑老公有什么艳遇,为此他的女人很沮丧,也只好忍着。
天热,夜深人静老鼠和偷油婆在黑暗的洞穴和夹缝中憋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熬到天 黑,可是,又来了几个喝酒的人,他们在这折腾到半夜才走。老鼠和偷油婆才从黑暗的洞穴和夹缝中爬出来,这儿成了它们的天下。
老鼠本来并不想祸害人类,感谢人类将它们排在地支首位,心存感激,想与人类能和平共处,不想与之为敌。但是,一些可恶的文人骚客在闲暇无事时,将长相猥琐、尖面猴腮伙伴比作老鼠,相互寻开心。从此,这些言谈以讹传讹,一传十,十传百,传播开来,有不少人把这当成真事,把这些不实之辞,统统都强加在老鼠头上,又用它组成了更多的贬义辞,太可怕了。如:贼眉鼠眼,贼头鼠脑,鼠目寸光,抱头鼠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生儿打地洞等。从此,搞得老鼠灰溜溜的,只能偷偷摸摸晚上出来活动,再也不敢在白天招摇过市了,它们成了冤大头。
偷油婆也很气愤,明明自己有名有姓 “姓‘蟑’名‘螂’,全名叫‘蟑螂’”,人们却硬要叫它做“偷油婆”, 多难听,它从没偷过油,它也叫冤屈。蟑螂不全是母的,还有公的,怎么都以婆相称呢,不成了女儿国吗,叫蟑螂今后怎样繁衍后代?自古以来有那么多贪官污吏不去管,却拿这些无名鼠辈、小虫作为攻击的目标,越想越来生气。所以,夜里不知有多少老鼠和偷油婆(蟑螂)出来,将人们忘在外的食物上爬来爬去,懒得去吃,在上面排泄点“佐料”,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我越想越恶心,肚子再饿,也没了胃口,真想把这碗粉全倒掉。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大概认为我这是极愚蠢的想法,分明是在向我抗议。我只好将这些令人倒胃口的花生米一颗颗夹出来,堆放在桌子上。夹起米粉,在汤中涮了涮,见“汤”(水)为净,勉强吃了几口粉,尽管口渴,没敢喝一口汤,付了钱,准备离开了小店。
这时,土豆来到小店拿着个大茶杯来小店来倒开水,见我回来了,想过来打招呼。看到丢弃在桌上的花生米,明白了什么,过去小声地跟老板讲:“你怎把我们几个人吃剩的花生米放在乡长的碗里,你晓得啵他是省里来的。”老板愕然,对土豆说:“我又不知道他是谁,没肉末了,用花生米代替。”尽管土豆和小店老板讲话的声音很小,我听到了。我颇有绅士风度,莞尔一笑,头也没回走了……
晴空万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看样子又没雨下了。别说是庄稼都盼着下雨,我也望天老爷下场大雨,把马路洗刷干净。这两天在外办点事,在马路上走一趟,连钻进鼻孔的灰都是热的。
听说县里的民兵在附近架起了几门炮,发射碘化银弹,击中了雨云,经风一刮,要雨的地方没下雨,早稻谷的晒谷场不要雨却一个劲地下,使人猝不及防,帮了倒忙。我惦念着夏家村在山田里种的一季稻,正是需要水的时候,现在不知怎么样了,要抗旱吗。
这时,刘小佳手里拿着塑料壶,带着一群村民,到了牯背岭。刘小佳见我后,像老朋友一样向我打招呼,接着说:“牛乡长,不对!应当叫‘牛老弟’,我们这些村民都是落实了你的指示,不抛荒。可种了稻谷,缺水。你也知道,平价柴油只要几百块钱一吨,议价柴油要一千多块钱一吨,贵了几倍。卖的粮食是平价的,我们买不起议价柴油。你是省里来的,麻烦给批个条,买点平价柴油,不多,只要百把斤柴油。”我听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套,倒抽了口凉气,从哪儿去弄这百把斤柴油。附近有几处加油站,都是所谓市场调节价,那来的平价油。但是,我又很快镇静下来。对他们说:“别着急,你们休息一下,我先去问问情况,再答复各位。”
我找到办公室的文秘书,问他,这种事以前是怎样处理的。他告诉我:“乡农机站还存放有柴油,准备抗旱用的,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你写个条,让他们去农机站买。”“我批的能算数吗?”“农机站会卖给他们柴油?”文秘书笑着说:“放心,他会的。农机站的站长是乡人大代表,你来担任副乡长,要经过乡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后,县里才能下文。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我如释重负,赶快写张便条,还是有点不放心,请文秘书在便条上加盖乡政府的大印。看了看,认为不会有问题,回住房的道上,脚步轻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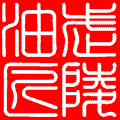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