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留守知青
大木子、小木子、小荣常来和我聊天。大木子问我:“牛副乡长,你在城市长大,怎么对农村的事情这样熟悉。”“我呀,上山下乡当过六年知识青年,在农村学到了一些知识,想不到这些知识能在这儿派上用场。”大木子说:“知识青年不是都回城了吗?为什么在我驻点村附近的县林场还有个知青。”“这个我晓得,那是他在这里和一个女人家结婚留下来扎根了。”小荣回了话。我听他们说这儿还有知青,出于好奇,也可能出于对这位兄弟的关心,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他。我对大木子说:“明天看看他去。”“好!不过这件还是我在村干部那儿听说的,他们熟悉,我先去给张村长打个电话,要他给我们带路。”大木子去打电话和他俩约好,明天去看那位知青朋友。
第二天,我们仨人正准备出发,小荣突然被叫去办其它的事,我与大木子上路了。骑田岭林场离牯背岭约三公里路程,不到半个小时到了村口,张村长早就候在那儿了。他带着我们朝骑田岭方向走,边走边介绍所知道的情况:这位知青叫根生,是长沙下到县林场的,现在,县林场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也像乡镇一样将土地分给了职工,知青也分到了责任田,和村民没有两样。去他家要路过他家的责任田。问及他为什么还没回城,张村长说:“他从小没见过父亲,他的父亲早就过世了。长沙也没有家,在这儿结婚,在农村扎根了。”
我们翻过小山包,眼前一大遍开阔地,地里有人正准备种秋季作物。张村长赶上来,指着远处的人对我说:“他在前面,你看,就是那个挥舞锄头挖土的人。”然后,张村长敞开喉咙大声叫喊:“根生,根生,来客人啦。”我远远地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好像是听到了有人在叫唤,大概是要找他,他心里大概在纳闷,我那有客人来?不过他还是缓缓地抬起头,迟钝地转过身来,仿佛看到了我们这群人。随着俩人间的距离渐渐缩短。我大致能看清楚他的轮廓,他和当地的村民根本没有区别。走近一点,能看清他衣服上的补巴,头上零乱的毛发,像秋天荒坡上凋零的野草,随秋风吹得轻轻地摆动。再走近一点,看到了他满脸刻画着岁月的苍凉,劳碌困倦的双眼好像只能睁开一条缝,眼球浑浊像生锈轴承中的钢珠,吃力地滚动。他穿着件卡几布学生装,洗得发白,被无数补丁叠盖,特别是双肩补丁迭盖一层又一层,屈指一算,这件衣服有年头了,大概是下乡时,母亲倾其所有给他缝制的。他下乡后只是过年过节,难得的休假日里,有机会去县城看热闹,才舍得拿出来穿在身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早就超期服役了。破旧了,忍痛作为劳动服,天天穿在身上参加劳动。现在捐献给灾区,都没人想要了。他年纪与我相仿,四十岁上下,头发花白,脸上没有半点表情,可能他忘记了自己最后那次露出笑容的准确时间,像个五十出头的病汉,用锄头把撑着自己的身驱吃力地望着我们,他的行为与实际年岁相距太大。
我赶上前去笑着用长沙话问他:“你是那年来的罗?是那个中学下放到阁里来的罗?”他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或已经不习惯听长沙腔,不知他为什么没有答理我。大木子用宜章话接上问他:“根生,这是牛副乡长,原来也是个长沙下放的知青,听说你也是知青,特地来看你。”他听懂了大木子的话,冲我们一笑,模样难看,是苦笑。我见到他这付模样,是他对世上的所有事物都麻木了。我觉得自己的心上在伤口在流血,流出了好多血,没法止住。他用宜章腔对我说:“你好,忙啵?”我告诉他,在这郴楠乡工作,有事去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我站在他身旁,像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谈起,想他应当邀请我去他的家看看,我很想见到他的孩子、妻子和居住的地方。他开口说了“你好,忙啵?”这句话后,再也不开口说话了,木纳地望着我们,我觉得无聊,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可能是他不愿意耽误了时间,朝手上啐了口水,像抹润手霜那样,在手上抹均匀,握紧锄头,又迟钝地转背,去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今天他不干完地里的活,可能“周扒皮”会不给他的工钱,他全家就会饿肚子……
我眼前所见,心情特别复杂,希望见到的是个梦,却又是件真事。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回牯背岭的路,有种莫名的滋味涌上心头,这种滋味根本无法说清,应当怜悯,应当愤怒,应当呐喊,还是应当流泪。我就想跑得远远的,狠狠地朝着棵大树抽打,发泄心中的郁闷。我的理智终于压住了。宽慰地对自己说,他可能早适应了这种生活,不想去改变它?我又顿生疑虑,怎么这解释不通。
一路上张村长与大木子再没说话。我想了很多:艰难的生活环境能使人更加勤劳,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去改变眼的一切,也使人麻木,随遇而安,吃泥巴罗卜,吃一节,揩一节。我只觉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润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我们不是救世主,不知究竟能帮助他些什么?愿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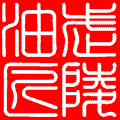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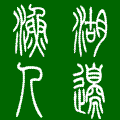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