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六)人道忌全
伍奎良在一九五二年底参军,在新兵连接受训练,作为入朝参加战斗预备队,时刻准备参加战斗。他并不知道中美双方正在进行马拉松似的谈判,虽未入朝,仍叫做自愿军是当之无愧的。与其是否参加过战斗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一九五五年,他和公社老书记从一个部队复员回来。他可以在城里分配工作,端起铁饭碗。他却一心想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听老社长说,土改工作队走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这样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
当时还没有修通公路,很多群众没有出过这村子,能去趟县城都算得上是人生中一次了不起的经历。对电灯电话是何物都没听人讲过。更不用说耕田不用牛了。社员们只知道,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牛就是用来耕田地用的。牛不耕田了,它们今后去干什么,杀了吃肉,太可惜,真有点为它们今后的出路而担心。点灯要用油用电。电是什么东西,要多少钱一斤,买回来用什么装,还要用瓶子装吗?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听起来都觉得是在讲神话故事很新鲜。社员们认为伍奎良不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些东西对他不陌生,他还到过北京、省城、听说还到过朝鲜。不但见过电灯、电话,拖拉机,还坐过坦克。社员群众都佩服他,认为他什么事都知道是个能人,有土改的工作队员那样的水平,选他当了高级社的副社长。
现在,村里通电了,家家点上了电灯,村民们告别了用油点灯照明的历史。村部也装了电话,只要摇把一摇,远在几十里外的总机就会帮你转出去,接通要找的人。又要换自动电话,只要知道对方的号码,全国各地都可以通话了。耕田不用牛也实现了,丘陵区,田地面积小,只能用小型拖拉机,但这玩艺儿耕地总做得不那样太干净彻底,有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耕不到,山田还得用牛耕地。不管怎么样,通过几十年的干社会主义,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都实现了,没吹牛。特别是这些年,不少村民盖起了楼房。真是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社会主义大慨就这模样。
伍奎良扪心自问,在这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也干过不少蠢事,有主观的,有客观的,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傻得可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伍奎良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的学龄前儿童多,学校缺教室。伍奎良提议将村口的庙拆掉改建教室,有人怕得罪菩萨会遭报应。他不信邪,说干就干。菩萨有嘴也不能说话,拿他没辙,几十年过去了,他也遭到报应,至今仍还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现在,又听到有人在说:“那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庙,是文物,拆掉了可惜。”
年轻人要思想解放。过去的耕作方式太保守了,禾苗间距、行距太大,应当密植,将原来插秧的九九寸,改为三三寸,这样每亩可多种一倍的禾苗,一亩当成了二亩。在改革传统的耕种方式的问题上,不少有耕作经验的老农,反对年轻人提出的密植意见。长辈们打了个比喻给伍奎良听:“一碗饭只够一个人吃饱,二个人只能吃半饱。同样,一块田硬要多插秧,肥供应不足是不能高产的。”伍奎良虽年轻,但从小在农村长大,世代务农,在指挥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伍奎良认为他们讲得有道理,又不能不听上级的话:要解放思想。又不能丧失理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模棱两可。
他思前想后,没急忙在全大队推广密植,而是根据部分人的意见,先搞实验田,他认为这样自己可进可退。插秧时,他下一道指令,让大队小学老师给学生放插秧假,全到实验田来插秧,大搞人海战术。他一方面希望试验田能够获得成功,一亩田能当两亩田,当然是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又在寻找退路,万一在全大队推广搞的实验田,失败后损失就太大了,社员们要挨饿,自己也成了罪人。
他心里清楚一亩田当两亩田用就不能缺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应当多施基肥,增加追肥。他毫不吝啬把实验田里的基肥放足,又多次追肥。有的老农看了后,头摇得像拔浪鼓似的,这是在糟蹋了肥料。对伍奎良说:“还嫌肥少吗?把秧苗插到屁股里,省事多了。”禾苗转青,他又优先安排劳动力薅了两次,俗话说稻薅三遍,肯定好。稻还没来得及薅第三遍,实验田早已青郁郁的,插足不进去了,比按照常规种植的水稻高出了很多,他暗自高兴起来在心中盘算:农民最讲现实,实验田成功后,用不着开会动员了,年轻人会欢欣鼓舞,庆祝胜利;长辈们也会心服口服,按年轻人的意见办。全大队都会自觉地按密植方法耕种。那么夏家村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粮食翻了一番。不只光靠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才增产粮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样是有很大潜力的。这才叫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算真正的大跃进了。伍奎良高兴得早了点,丰收在望,并非丰收在握。其它稻田在拔节孕穗时,实验田仍在一个劲地疯长,其它稻田在灌浆泛黄时,实验田还是青郁郁,尔后,全都倒伏了,只在稻尖上长出了几粒瘪谷子,稻草的产量确实高于其它的田,可稻草代替不了稻谷,搞的实验田失败了,他还是暗自庆幸。
伍奎良参加公社组织的《人民日报》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学习,深受鼓舞,又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特别是有的地方放卫星,亩产上万斤,简直是个神话,他想都是种田人,亩产多少应当清楚。亩产能有万斤吗?这些人又不反过头来想想,这一百担谷,堆放在田里像座小山一样,把稻草连根拔起与谷合起来过称,也不到一万斤,除非把稻田的泥巴挖下去一层,当作谷子过称,才能凑足份量,吹牛皮得靠谱。
有的基层干部心里明白,不跟着瞎起哄,但又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默默无言,不敢讲真话又不讲假话,坐在那里学习难受极了。有些人昏了头,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跟着讲瞎话,瞎说不犯法,他们还受到了表扬,当上了模范。伍奎良选择做前者,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过坎,又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说完假话脸又发烧。
那年,尽管大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全体社员积极抗旱,还是夺取了较好的收成。待稻谷收割完毕,伍奎良根据各生产队入库情况,逐个核实,那些甲类田,不管怎么算,每亩也只有六百多斤,那些山丘冷浸田,还不足三百斤,按理说是丰收了。但是,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不足五百斤。怎样上报今年的粮食产量?成了伍奎良的一块心病。如实上报肯定是过不了关。为此,他召开了大队干部会,大家一道合计。有人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就报五百斤,也有人主张按本大队最高亩产六百斤上报,还有的人了解“行情”,体谅伍奎良的处境,同意上报亩产八百斤。伍奎良默不作声,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拍板,上报一千斤。
大多数人都认为虽然这样上报,水份太大,不好收场。伍奎良坚持自己的意见,今年只有上报了这个数目,他才有可能顺利过坎。伍奎良叫老会计写好喜报,字迹未干,他就恭恭敬敬将喜报举在胸前,去公社报喜。伍奎良知道庆丰收个个村都会组织锣鼓队,他也拼凑大了一个锣鼓队,叫他们卖力地敲起锣打起鼓,要像过年那样热闹。
伍奎良上报亩产一千斤,走在报喜的路上,心里还是有些心虚。他在基层工作这些年来,从来没向党组织讲过假话。那时基层干部有句口头禅:“知心的话儿对党说。”现在,知心的话儿对能对党说吗?在责怪自己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为过这个坎,恬不知耻地谎报亩产一千斤,真不应去出这样的风头,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报产量呢,大跃进是为了鼓干劲,不是大吹牛皮。
他边走边朝两面围观人群张望,仿佛自己象生活在安徒生童话世界里,这张所谓“喜报”,是那位皇帝的新装。伍奎良不过是一丝不挂的裸体小丑。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越朝前走心中越忐忑不安。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大声地喊着:“夏家村大队真了不起,亩产千斤。”个个向他竖起大拇指,伍奎良听起这话,觉得多特别刺耳。仿佛他们不是在夸奖,而是说:“快来看这个人,他没穿衣服一丝不挂的裸体小丑,多丢人现眼。”伍奎良快走到公社门口,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大的傻子,为了荣誉所累,所谓的大跃进、而付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两只腿竞迈不开步,发抖;顿时,眼睛越看越模糊,觉得眼前黑洞洞的看不清前面是路还是无底的深渊。
伍奎良觉得特奇怪,全公社庆丰收报喜的日子,庆典是载歌载舞,载欢载笑极有凝聚力的大事,应当人声鼎沸喜气洋洋才对。今天怎么这样冷冷清清呢?没见到争先恐后的报喜队伍,而只有夏家村大队到了公社。公社书记接到夏家村送来的喜报,满脸的不高兴。平常这位长者见了自己都是和颜悦色,充满着对年轻人的关爱,今天可不对劲。现在见他那模样,仿佛恶狠狠地对伍奎良说:“你太让我失望了。”伍奎良觉得非常郁闷,吹牛被识破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夏家村大队上报亩产一千斤,公社领导会不会批评他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一连串的问题和为什么,伍奎良在反复地问自己。他非常自责这叫什么大跃进,这叫大丢人!
不久,听到外边传来敲锣打鼓和鞭炮声齐鸣。各大队报喜的队伍接二连三地到达了公社,产量依次一个比一个高,后来的几个大队,竟报出了亩产五千斤的高产纪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神的功效!终于有大队放出了高产卫星,公社书记紧锁的眉头总算舒展开来。伍奎良看到这些喜报,心里反而平静多了。在总结大会上,公社书记严厉地批评了伍奎良说:“夏家村思想保守,没有革命干劲,是个小脚女人,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迈不开大跃进的步伐,夏家村大队是后进队。说严重点,伍奎良是右倾思想在作怪。大家要好好帮助伍奎良。”几十个大队干部全都拥过来,团团围住伍奎良,进行帮助浪“汤圆”(农村惩罚人的方法:将人围在圈中间,你推我搡,使站在中间的人东倒西歪,头昏脑胀。有个别心存芥蒂妒忌他的人,乘机暗下阴招,打他几拳。)这就叫“帮助”,伍奎良虽年轻,但因牛吹小了点,受到了惩罚。伍奎良没有怨言,自己迷惑不解,这是为什么?
伍奎良被弄得鼻青脸肿,在回来的路上,问几位年长的支部书记,你们的产量是怎样算出来的。他们听后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这要感谢你呀。我们派人在路上打探,见有人报喜,回来报告。根据你们大队报喜的产量,在数目上加码,自己才逃过此劫。你年轻,不找你这个垫背的,难道要我们这帮老头去当“汤圆”,去接受帮助吗。我们这些老东西可经不起这样的帮助。如果我们站在中间,被这一伙人“浪”几下,非把这幅老骨头架颠打零碎不可。伍奎良恍然大悟,自言自语地说:“哎!姜还是老的辣。”
公社书记与伍奎良都是同年转业复员的军人,看他年轻,本想好好培养他接好革命的班,还回可让他太失望了,没有鼓足干劲,还要他在基层多锻练几年,狠狠地批评了他吸取教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伍奎良作垫背的“老姜们”失算了,他们先拿别人垫背,自己也成了垫背者。公社支持灾区,搞一平二调,调走了几个高产大队的粮食。他们哑巴说黄连,没处诉苦。社员可遭罪了,还没等到过年就无米下锅了。夏家村是后进村,粮食产量最低,未征调过头粮。伍奎良虽然受到“帮助”, 歪打正着,夏家村的社员保住基本口粮,饿饭的群众比其它大队少,为群众办了件好事。伍奎良虽自受了点委曲,谁都不怨!觉得值!
伍奎良长见识了,祸福是相依的。后来几位年长的支部书记都得了水肿病,拖着肿得发亮的双腿对伍奎良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我们谁都莫怪这叫自作自受!遭殃的是社员,他们受苦了!”在这事件中,基层干部都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教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他的表现,许多事情并不是基层干部他们造成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去改变的,他们只能去适应环境。后来,农村瞒产私分出笼了,就是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所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有它的前因后果关系,不应该对已过去的事情去评价如何展开才会合理,而是要说历史是如何展开,如何终结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
伍奎良每次回想起这些往事,又情不自禁地好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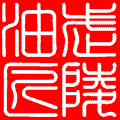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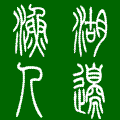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