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响应富裕中农的号召,写写1968年。
1968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正是我们高中毕业,考大学的一年。文革一来,一切都改变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无书可读,复课闹革命也是一句话。正如老团兄说的“复课”还是干打雷,不下雨。
下半年66,67届的同学有了几个面向,进工厂,当兵,“出身不好”的下农村。我们呢?以后到那去?看看天,看看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谁能回答。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时,老人家一道圣旨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那还有什么话可说,一个面向接受再教育,修补地球。那段日子班上同学在一起就是议论下农村的事,开会也是动员大家积极报名去广阔天地。说真的,听说下农村没觉得那么可怕,在家闲得有点无聊,有劲无去使的日子并不好过。何况农村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进了中学,每学期都下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农活也干过不少,集体生活也好玩,既然老人家发了话,不去也不行,那就高高兴兴的去。
下农村有几种形式,有随农村来的同学回到他们家乡的,也有投亲靠友的,这好像都不适合我,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喜欢集体生活。于是选择了随学校大部队到农村插队,学校集体插队两个地方,湖区到沅江,山区奔靖县。去哪呢?那时老爸还关在牛棚,听说我要下农村,搭口信回来建议我去山区,当然最后由自己拿主意。于是几个玩得好的朋友一起商量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山区好一些,主要是湖区华佗无奈的小虫何,我们也怕,虽然“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了,残渣余孽还存在。再加上先去靖县的朋友回来一游说,我们就和靖县结缘了。
回家一说去靖县,家人一致同意。下一步准备简单的行装,妈妈特意给我做了一件黑白格子的确良衬衣,现在的确良无人问津,当时可是奢侈品,我当宝贝一样的收好,轻易不穿。老爸虽然关在牛棚,还是很关心我的去向和前途,特别叮咛,要带书下去读,不要荒废了学业,学了知识将来一定有用,所以带的行李最多的是书,有高中课本,有辅助书籍,小说。
那些日子我们跑学校较多,一是办手续,分配到队,二是和同学们告别。到靖县甘棠公社是铁定了的,到那个大队,生产队还需考虑,年轻人火热的心,不知天高地厚,满腔热血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刚好乐群10队,12队(到顶山)第一批都安排了知青,11队分得散,没安排,而队上要求派知青去,那里是大山区,比较艰苦,来接知青的吴若东社长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因有到顶山的同学做榜样,10队也有玩得好的同学,我们没有犹豫的回答:愿意。记得赵胖子当时还特别激动说:我们不怕苦,我们有力气。张公猫,周头,曙老倌还有一帮同学围着吴社长问这问那,肖和我几位女生站在一边听他们说。
明确了目的地,随后到派出所迁户口,那是1968年的12月底,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户口本上被注销时,心里还是斟了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受,难受?(离开亲人,离开长沙)莫明其妙的兴奋?(开始一种新生活)?茫然(前途未卜)……说不清到不明。
1969年1月6日,我们打起背包,告别亲人,告别长沙分乘五部大客车,还有两部装行李的货车,从一中出发,浩浩荡荡的奔赴靖县甘棠公社,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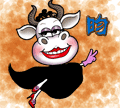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