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沙方言如何记字
说起“长沙方言”,“是”长沙人都晓得讲,哪怕是学前幼童也能讲得“一烙流”,哪里载得一个人来开坛论道呢?这话讲得不无道理。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听你讲。他们最想听些什么呢?一是他自己只会讲却有很多字不会写,所以他想听你讲“本字”;二是他想听你讲“长沙人何解会是咯样范讲”。对于探讨这两个问题,许多人饶有兴趣,热情不衰。
那好,本开篇文章就先来讲讲“本字”,但我这里要稍稍把话题延伸一下,那就是长沙方言究竟如何"记字"。至于第二个话题,要放到以后单独去讲了。
所谓本字,就是原本所造之字。但是,本字并不一定为仓颉所造,也不一定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记录和解说过的字,很多是后来的某朝某代造出来的。年代不要紧,关键它要是最早一个出现的。
对任何事物,人们总是抱有追本溯源的极大兴趣,对于汉字,也想一个一个的“考”出它的本字来。
在人们现时使用的语言中,一个单音词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个对应的字来记录它(也有"有音无字"的情形)。下面分五种情况来说说。
第一种情况是,这个字就是本字,自古以来便是这样写的,谁也不会怀疑,例如人字;
第二种情况是,可能不是本字,但人们并不怀疑它,早已习惯于这样写了,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就该写成这个样子,例如满崽的“满”字;
第三种情况是,估计不是本字,但是不知道本字是哪个,“管他的,先咯样写哒着,反正习惯会成自然”,例如策神的“策”字;
第四种情况是,明知不是本字,因为本字考究不出来,只好来个“同音借代”,也就是写“白眼字”(别字),例如“纠麻的”的纠字和麻字;
最后一种情况,不要说本字连同音字好象都写不出来,这是最头痛最急人的事,“不晓得要何什搞才好”,例如“吓得‘噤呤哐啷’”。这个“噤呤哐啷”是我个人的一种写法,不一定人人都同意这样写。
第一种“就是本字”的情况当然不须去说了,要说明的是后四种情况。在这之前,还是针对本字说明几个我认为是基本的观点吧。
一、方言中的口语词(单音词),不是都有本字可考的。
这里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汉字体系根本上是建立在“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基础之上的,并非为各地方言土语而设计。二、口头语的变化发展永远都走在书面语的前面,口头语的词汇也远远要比书面语丰富,口头语于是跟书面语总会有些脱节让后者跟不上,所以,书面形式的文字用来记录不断变化的口头语也就难免有点力不胜任,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二、不要刻意去考本字、写本字,写不了本字既不丢丑也不奇怪。
本字从来只是专门家(也可能包括爱好者)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成果得到认可和普及之前,人们尽管按照“约定俗成”这个大原则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必顾虑是不是写了本字,不必害怕人家说你写错了。当然,你若有本事做到与众不同,你写出来的就是跟大家写的不一样而又能被多数人所欣赏,那你的功底、你的品位或许就跟着得到了显现。例如,人人都在写“作古正经”,你却写成“捉古证今”或“作鼓震金”,你拿得出你这样写的理由(“抓住古代的事例来证明今天、眼下的情形,平常小事一桩值得这样去做吗?”“也就是‘击鼓鸣金’而兴师动众,普通事体何须如此煞有介事”)又能让人家接受,而且不妨碍人家理解,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三、有些本字虽已有人考出,却并不一定要拿它来记录语言。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本字是冷僻字,难写难读,跟大众肯定过不去,你看它时只能“干瞪眼”,或者虽不是冷僻字却让人看着就感觉别扭,怪怪的,心里头挺不舒服。
如果大家觉得上述三个观点还能接受,我们就继续往下说长沙方言究竟如何记字。
1、自造方言字“似乎”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据说,“搞”这个字,就是夏衍先生在抗战期间桂林办报时所造。大概他觉得“做”“干”“弄”“整”这些字都不能贴切反映西南方言区口语中“gao”这个词的情趣,于是根据“形声”造字一法造出了这个搞字,后来慢满在大众之中传播开了,终于取得合法的地位。在香港,“势力强大”的粤语自造其字更是蔚然成风,几乎随心所欲,大家觉得这样很方便,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可大摇大摆登上媒体的大雅之堂,尽管不懂粤语的中国人看着这些方块字是“一头雾水”。如果我们可以仿效此法,许多记字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例如,长沙话表示蹲义的“gu”这个动词,记字不妨写成左为足字旁右为一“古”字;表示瘸义的“bai”这个动词,记字不妨写成左为足字旁右为一“拜”字。其余类似情况,亦可比照此法类推。相信这种形声造字,长沙人在心理上也是完全能够认可的。不过,如此所造之字简直无望成为规范汉字,不比方言的“造词”有可能为普通话词汇所吸纳而正式进入词典(如“霸蛮”一词)。所以,方言造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2、同音借代才是行得通的普遍做法
例如,表示倾义的“kuan”这个动词,依照形声造字法,可将“框”字的木字旁改为提手旁就是。现在,因为没有造出这样一个字来,多数人就用同音字“筐”来替代,如记录“筐瓢”一词。要知道,方言写作主要在于表现“一方之言”的特色,这种特色是透过方言词而不是方言字来体现的,同音词用来表现方言特色也是可以胜任的。只是建议在使用特殊意思的方言词时加个引号,以防读者误读或“淡看”。不过,同音借代之法也有其不足,这就是并非每个方言音节都有对应的通用汉字,所以不少时候你无法找到替代的同音字(这也正是人们之所以想要考本字和造方言字的原由吧)。没有同音字(包括音近字),这才是最让人感到困惑的。
3、放心使用通用汉字
有些方言词,其特色仅在语音而不在语义,不存在使用方言字的问题,就放心使用通用汉字好了。例如普通话的“砧板”一词,长沙话发音为“dinban”,于是有人干脆就写成“钉板”。这里的“钉”显然只是借用的同音字。砧字被人写成钉字,只是因为砧字在砧板这个词中长沙话要发音为“din”。现代声母z、zh在古代是发音成d或t的。这就是说,砧板被长沙人读若钉板是保留古音的结果。这种语音现象当然远不是孤例,又例如单音词“震”读音为ten(例:“路太不平哒,单车不好骑,ten起好厉害。”),“粘”读音为diang(例:“手上diang巴diang巴的”)。再例如,“何解”“何什”的何字,长沙话读若“禾”(o),就不要写成“禾解”“禾什”。在其他的许多南方方言中,这类古音被保留下来的情形更为普遍。
4、已经约定俗成的写法不改无妨
特色只在保留古音的方言词,有的已被人按现代普通话(不是按长沙话)写成了同音字。例如前文提及的满崽的“满”字,应该说是写错了字。这个满字,长沙话在很多场合里是不读成man这个音的(man的读音明显是从普通话里学来的)。长沙话里读为man音的满字,它的意思是“排行最小”,而“排行最小”也是普通话“晚”字的一个意义(境外电影《晚娘》中的晚字就是取的这个意义),晚字的古代读音是前面要加上一个声母m的,所以晚字的古音正好读若“满”音。这样看来,“满崽”实在应该写成“晚崽”,这样于音(古音)于义皆合。但是现在既然大家都写成“满”字了,就不必因为写本字便改回到“晚”字。又例如,“策神”的策字,我以为从本字的角度可写成“扯”(请参看拙文《策、择、扯,究竟写哪个字好》),但是大家已然接受了策字的写法,那就继续写这个策字好了,不改亦无妨。
其他有关具体的记字话题,以后再一个个的跟大家一起探讨吧。
(续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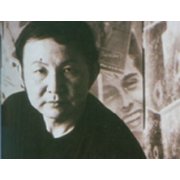








 叶哒勺本字鹅事搞罗!大旗教授开完会冒罗?开港罗,我们等得好糙人弟!
叶哒勺本字鹅事搞罗!大旗教授开完会冒罗?开港罗,我们等得好糙人弟!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