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料的故事
那一年,“学大寨”运动是越搞越凶了,全国各地没有“虎头山”也要上山下湖跟大寨人一样“战天斗地”,除此之外,就是抓紧“狠批资本主义”。郴州临武县的批资本主义,就是严禁大肥用到自留地里。具体做法就是社员自家的茅厕一律归公,从此不准去舀只能去蹲。以前的做法是,自家平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到月底了,队长哨子一吹,各家统一“出肥”,你就可以看到几十担装满粪便的尿桶排成一溜,大家再凑在一起一担一担按质定级、过秤计分。现在茅厕归了公,大肥的计分办法也就有了相应的变更:按屁股计。大人大屁股,一年下来14分工;小孩小屁股,按一半计也就是7分;至于学龄前儿童,因为没有哪个会去蹲茅坑总是四处“屙野屎”,所以没有屁股不计分。知青本来就没有一个有茅厕的,也就从来没得过肥料分,现在改为按屁股计分了,自然心中有几分高兴。
每到年底统计工分了,各家就派一个男人做代表去队里开会。什么干部都不是的这些普通社员,真的是把这一天看做跟过年差不多的开心日子,脚穿“鞋头水袜”,手提炭火烘笼,跟干部一样一屁股坐在那里,可以不声不响,也可以大喊大叫,关键是这一天不动不挪工分照记,享受队干部的待遇!我也坐在那里,我就是我不代表别个,我拿张湖南报在看。这会开着开着讲到肥料计分的事来了。队长说,没有什么好讲的,把每人的分加上去就是,大屁股14分,小屁股7分。停了一下子,忽然有人冒出一句话来:“大家看看,大旗算个什么屁股好哇?”我正举起报纸在看,听声气也知道是副队长四赖在发问。“大旗算个什么屁股好”——好笑,我都20几的人了你们冒看见哪?我把气瓮得心里不发,先看看他们会怎么议着。四赖以为我在看报没有留意,就继续说:“大旗的屁股有点难算。过年咧,回他屋里去了,屎是肯定屙得长沙了;平时咧,总比我们要多几次去赶闹子(赶集),屎又屙得街上了。照我看,算个小屁股算了,反正知青也不在乎这点工分……”听到此处,我放下报纸露出脸来,冲口回他一句——“我在乎!”这冲口一句把四赖吓了一跳,其他人也都不做声。这时,我须要为自己不能算小屁股进行自我辩护。我就说,一个月六个闹子我难得去一次,也是工分要紧要出工的,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但是,每个闹子总会有几个山里头的知青同学路过我们村子会在我这里自己打开大门生火做饭吃(我所在的大刘家村靠县城最近,我又住在村子口上,我的门钥匙是特为同学们准备的就塞在门口的砖缝里),他们吃了我的饭总有人要到队里的茅厕屙屎,这么多人还抵不得我过年回家那一个月?我这样说过之后,不等四赖插话,队长马上表态:“大旗也按大屁股算!”再也无人敢讲空话了。于是,我当年的这一维权行为替自己争得了14分肥料工分,大概也能值5毛钱吧。
茅厕归了公,大肥不能用,社员的抱怨是自留地的萝卜白菜如何能长得大。所以,小肥也就是尿自然变得金贵起来。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就是很看重自己的小便的。每次出工之前,一定会先躲在门角湾里对着尿桶屙个尿。出工在外也是极少“屙野尿”的,多是霸蛮夹住挨到收工回屋再屙,所以不免经常出现尴尬之事:一路上谁都不敢去搭理,只顾得急匆匆赶到屋门口急匆匆开大门,人一进门就躲到门角湾里去了。为肥料事,我是伤透了脑筋。
我这里在伤脑筋,希法在那里开始为我动脑筋。希法是队里的政治队长,20出头的后生伢子,人灵泛得狠也和气得狠,跟我关系特别合事。有天晚上在队里记完工分,他突然对几个后生说,“走,到大旗屋里听他‘讲牙告’(扯谈)去!”于是我被他们簇拥着回了屋。一进门,他就拿起竹端子从水缸里舀了一大端子井水咕噜咕噜喝下去,这才坐下来听我谈今说古。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吆喝着起身回家睡觉。这时只听希法说道,“不要慌,每人帮大旗屙个尿再行(走)!”我对希法说的这句话感到很诧异,几个后生伢子却都听明白了,都等在那里排队屙尿。屋子里顿时弥漫开一股尿臊气,我的心里竟是想着这一下尿桶里的尿不知会升起来多少。尿臊气终于没法破坏我的愉快心情。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希法他们晚上都会来,进屋就是人人先来一端子水,临走人人都会留下一大泡尿。我的自留地里的小白菜,从此渐渐转黄为绿,终于出现了生机。
1972年底,我要远走高飞去怀化修枝柳铁路了,我准备在那里舍死忘命的大干一番,争取能留在铁路上。临走那天,我把所有的农具、家具、炊具和碗筷都送了相好的农民,最后时刻是希法跟那帮后生伢子聚在我那里帮我捆扎行李。最后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门角湾里还有半桶尿,我对希法说“你拿去吧”。希法说,“好的。你再也不需要了。”说这话时,他还扮了一个我能读懂的鬼脸。
至今,我还记得希法扮的那张鬼脸,还有他拿起竹端子咕噜咕噜大口喝水的可爱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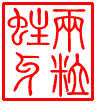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