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背景说明:
这篇文章写了多年了.当时,长沙晚报准备用一期"百版专刊"迎接新世纪.其中一个版专写所谓"遗憾"之事,由副刊部主任刘小莽负责.他向我郑重其事的约稿.我既看重这个专刊也看重老朋友的邀约,所以想了很多天也迟迟没有提笔.最后决定写这个"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当年以为我见到了毛主席,几十年后才知道真相:老人家那天根本没有去机场.这还不"遗憾"吗?稿子写成交给小莽.几天都没有答复.我觉得怪:这样的"重稿"都不行吗?再等等吧.又过了一些天,他来电话"遗憾"的告诉我:"写得太好了,你是写下了'世纪的遗憾'哪!但是老总那里通不过,说是'刊发出去要出大事的!'.我实在没有办法呀."现在发在我们知青网站,看看是不是会出什么大事吧.
“最最----最最幸福的时刻”。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典型的文革用语,说的也准是与伟大领袖沾点边儿的事。
1 9 6 6年8月1 8日毛主席破天荒身著戎装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广场上那些突然冒出来的红卫兵,从此后谁做梦都想能有幸被他老人家检阅一次。那可是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呀。那一年我1 9岁,读高三。1 1月中旬免费乘车大串联接近尾声时,我这个不可“乱说乱动”的“黑五类”才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路颠簸总算也到了革命的心脏北京。
一出北京站就见大横幅拉着一 “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顿时眼泪就流了出来,旅途劳顿也即刻烟消云散,心里便琢磨起究竟什么时候能见到伟大领袖。当时,毛主席已先后检阅过7次红卫兵了,可北京城里满眼仍是尚未受阅的红卫兵,一个个都“不见主席誓不还。我被安排在北京化工学院住下来。直至1 1月2 5日,才听广播说毛主席当天又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我们这些人一下就着了慌:下一次又得等到什么时候呢?
谁知这晚睡到半夜两点时分,也就是2 6日凌晨,幸福突然降临。接待站的军代表突然让革命小将们赶快起床紧急集合。一位长官激动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最好最好的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要接见我们了!大家一听高兴得直叫直跳。我们按要求在半小时内飞快地吃完饭、领好白天要用的食品一4个面包、4个鸡蛋和4个苹果,然后迅速整队集合。大操场里黑压压几千入居然鸦雀无声,静听着军代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训话。
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临出发前军代表要求大家两人两人一组地相互检查并担保对方确实没带任何小刀、别针、钉子一类的锐器。完了,接受检阅的队伍便在寒冷的夜色中雄纠纠地出发了,没入告诉我们目的地是哪里。走了好一阵,仿佛听见有入轻声在说“这不象是去天安门”,我无心探究,心里只被崇高感动着,耳里也只有齐刷刷的脚步声。队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送走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也不知到底走了多远,反正走到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倒是一点也不觉得累。
目的地居然不是天安门广场,是西郊机场。望不到头的跑道两边的空旷草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人手握红宝书席地而坐。紧靠跑道坐着3排维持秩序的军入,往后排过去的红卫兵至少在1 0 0排以上,事后得知当天在机场受阅的人数达百万之多。偌大一个机场,成了红色的海洋,歌声的海洋。小将们在军人的指挥下一刻不停地唱着革命歌曲,朗诵着主席语录,就这样等待着那个幸福时刻的到来。空气中满布着欢乐激动的分子。
我最初是坐在远离跑道的最后那几排,人坐得越靠后视线反而越开阔。4时过后,坐在最后面的人最早发现跑道尽头似乎出现了车队的影子,于是忍不住先一下都站了起来,眨眼间又开始使劲朝跑道那边挤过去。我们这些人终于失去理性不顾一切地脚踩前面一排排端坐者的肩背和脑袋快步前行,跟着就听一片尖叫声起,坐着的人便从后往前也开始一排接一排地站起来,于是秩序大乱而近乎失控。隆冬时节的北京,下午4点时分本已暮色苍茫,加上百万之众蓦地一下由坐而立而行,但见黄尘鼓舞,盖地遮天,整个机场几乎什么都看不真切了。奔突、骚动的人群最终还是被前面那几排军人组成的坚固人墙死死地挡在了跑道之外。我借力于人潮挤到了紧挨军人的位置。就在这时,车队开过来了。旁边有人嚷道“4点1 6分! 4点1 6分!”我忽然听见象是周总理的声音在大声呼唤:“同学们请坐下!同学们请坐下!”我赶紧瞪大眼睛想能看清伟大领袖的慈祥面容,遗憾的是竟连他老人家的身影都无法辨认。但我当时仍能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暖流从我心中淌过。兴奋而焦急的红卫兵开始了有节奏的呼喊: “毛主席一万岁!毛主席一万岁!”检阅车队就在这欢呼声中从我们眼前飞驰而去。车队一过,军人们在再也坚持不住了,跑道两边的人象两股洪流迅速汇聚一起,死命地追赶着逝去的车队。我的一只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踩掉了,结果我是一脚鞋子一脚袜子步行几十里回到我的住地的。一进屋,我就在红宝书的扉页上端端正正写下这样几行字:
最最……最最幸福的时刻——1 9 6 6年11且2 6日下午4时16分
终于见到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第二天,全国各家报纸图文并茂大版报道了毛主席第8次连续两天检阅红卫兵的消息。
从那以后,我不知多少次绘声绘色而又得意洋洋地跟年轻的朋友们介绍过我这一见到伟人的非同寻常的经历。有人问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总说“当然跟照片一个样”。
30多年后, 1 9 9 9年6月1 8日读到《南方周末》发表的《国庆庆典的幕后新闻》一文,我才大生惊诧生出好些遗憾来。文章介绍的倪天祚老人曾亲自参与了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下面是该文中倪天祚老人的回忆:
“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上级指示我们北京市委负责城内的2 0 0万,部队负责机场的1 5 0万,毛主席接见完城内的2 0 0万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主席的车直接开进中南海了。我把城内的2 0 0万人疏散完毕,没什么事,就到西郊机场去看看。这时机场的红卫兵还在焦急的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我看天色越来越暗,就对军区的负责人说:“天快黑了,这1 5 0万人,得赶紧疏散,否则天一黑下来,容易出事。’那位负责宣传的部长,怕主席没有回到中南海,有可能来机场,又怕疏散的队伍堵塞了主席的车,因此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返回指挥部,一到指挥部我就听说,由于天黑看不见路,机场的红卫兵在疏散的时候,有一辆车翻了,死了七八个人。”
附录:新华社北京(1966年)二十六日电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亲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胜利总结。
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首都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二十六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接见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太军。
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一百八十多万各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西侧的宽广大道两旁,以及西郊机场上,整个队伍象奔腾浩荡的红色长江。
下午两点三十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领导同志,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分乘敞蓬,来到了革命小将中间。
毛主席身穿军装,容光焕发,巍然屹立在第一辆敞蓬汽车上,向夹道欢呼的人群不断地亲切招手。多少人含着激动的泪花,多少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百万颗红心里进发出同一个嘹亮的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小将们怀着无限深情,目送毛主席乘车驰过去。
注:本则新华社消息先交代一句"一百八十多万各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西侧的宽广大道两旁,以及西郊机场上",后面用了一句"来到了革命小将中间"。这是在打马虎眼,掩盖了没去西郊机场的事实。当时是不可能有人看出这种“春秋笔法”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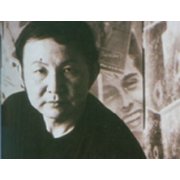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