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一词,是近年来很火很时髦的一个语词,随后出现的“决策学”也十分的吃香。决策究竟是个啥东西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是因为人们身边的那些“决策者”太过令人倾慕让人艳羡了吗?似乎不尽然。你看许多人那样痴迷的学决策,他指望获得的是什么?不是高高在上的“决策权”,而是超乎常人的“决策力”。即便是那些位高权重者,尽管决策权于他早已无须青睐,却也仍然希望自己的决策力能与手中的决策权相匹相配,至少不要遭人诟病,误人误己。
那么,决策之日兴是否跟策划之渐衰有关呢?君不见诸多策划公司这些年来已悄然改名为咨询机构,此中虽有“跟国际接轨”的原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业务不景气,所获欠丰厚。毕竟策划之士不过为人幕僚,只是“出主意”,其殚精竭虑后的思维产物最终还是要由别人来“拿主意”,取舍、定夺、拍板什么的由不得自己。古来即将出主意谓之“谋”,拿主意谓之“断”。谋而不断、多谋寡断或当断不断,今天常成了拿主意的决策者小觑出主意的策划人的主要理由。
让人不解的是,尽管满世界在把一个“决策”说过来说过去的,怎么学界至今竟连“决策为何物”都无有定论呢?撇开各种表述上的字面差别,在概念界定上至少也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决策就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出现的偶发事件进行紧急处置决定”。似这样强调“不确定”和“偶发性”,显然是要将决策限定为“冒风险的选择”。可是,除此之外的选择就都不能视为决策了吗?如此定义,未免狭隘。
二说,“决策就是对若干备选方案作出最终选择,是决策者的拍板定案”。
人们不禁会问:将决策限定为“最终的拍板”,那它跟“抉择”还有什么两样呢?虽然生活中确实有人会把需要作出抉择的事情说成“决策”,但那不过是简化了的一种说法罢了。“决策”有能力高低之分,“抉择”却没有。所以,人们经常会听到“决策力”的说法,但还没有听谁说过“抉择力”。
三说,“决策指的是一个包括提出问题、确立目标、制订方案、选择方案以及所定方案的执行这样一个全过程”。“方案的执行”怎么也包括在“决策”之内了呢?“执行”从来就是一个独立性质的重大环节,如同它不是“司法判决”的组成部分一样,它也不是“决策”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决策之时须要顾及日后的执行。“决策高明而执行得力”,这说的是两全其美,不是在说一件事。
还有第四个说法,跟上述第三个说法差不多,也是强调如此一个“过程”,但是未将“方案执行”归在其内。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才是可以接受的。
的确如此:“撰拟多个备选方案,通过分析、比较、权衡,最后从中选定满意型方案的全过程”,这就叫决策。在此,我们选用了“满意型”而不是“最优型”这样的字眼。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最后选定的方案,必定是决策者当时感觉满意的,而不一定是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最优的。
决策概念的上述真实涵义,也得到了汉语词源学的有力支持。从字的古义来说,决就是断(“决断”属于同义组合),也就是判定的意思;策就是谋,策划也叫谋划。如此看来,决策一词的现代解读,包含“谋”“断”二义而重其“断”,实在是精准诠释了古人的思想。“多谋善断”与“多谋寡断”,从来就被人视为两种境界两重天。若依决策的拉丁文写法 decidere 来看,其字面意义为“切断”。这意味着,决策要求人们在作最后抉择之时须断然撇开其他种种的机会。这跟中国古代的“舍得”之说又是相通的:欲得之,先舍之。
说到决策,不能不提到德裔美国人赫伯特·西蒙。这位理论大师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且是迄今为止作为管理学家而获此大奖的唯一人士,后来也是他奠基了决策科学。也许是因为兼有管理学家和决策学家的双重身份,西蒙针对决策所说的那句话是紧扣管理的:“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如今,西蒙寥寥数字的这一句话,早已被管理学界、决策学界乃至整个经济界的许多人奉为圭臬。看来,人们用不着再在决策一词的解释上喋喋不休的争论了。
至于决策的意义,或许我们只须记住拿破仑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就够了:“做决定的能力最难获得,因此也最宝贵。”他所谓的“做决定”,当然可理解为决策。这位不可一世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感叹呢?因为,有的决策使他戴上了皇冠,有的决策却让他流放到了厄尔巴岛上。
人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作好决策,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在这方面,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给人启迪、令人拍案的经典案例。你我这等人也有过不少大大小小决策的实践,想必不乏经验和感悟,说出来应该有人要听,听到了或许也有人会传的。
将这篇文章发在“天下知青茶座”里,我也是有所考虑的。我想,就如同人类的历史是由全人类的所有选择累积而成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是由自己对生活所作的全部选择(当然包括被迫的选择)之总合。明乎此,我们面对选择时不是也该慎重一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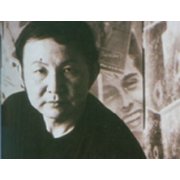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