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多子福不多
稻谷又黄了,村民们都在忙着做收割前的准备工作。我在乡政府值班,从外面来了位个子矮小的老人,面色黑中透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久被疾病折磨。他带着顶发黑的草帽,帽沿犬牙交错,只须轻轻碰一下帽沿,会掉下不少断草碎屑,戴这顶草帽必须小心翼翼,轻轻放在头上。它和他的主人一样饱经风霜,经不起折腾了。老人穿着件褪了色的空筒旧棉袄,纽扣全掉了,敞开着,裸露出枯瘦如柴的前胸,如两块干燥的搓衣板。手中拿着根擀面杖大小的杉木棍,一瘸一拐地朝办公室走来。
天气燥热,人穿短袖衫都嫌热,他怎么不穿件单衣?难道家中连件旧单褂子也没有?我赶忙上前去,扶老人坐下,又给他倒了杯凉开水,递给老人。老人接过杯子,情绪有些激动,对我说:“你是乡里的领导吗?我是夏家村的,要告状。”又有言欲止。我想老人像是受了委屈,可话到嘴边怎么又咽回去了,像是牵涉到了什么人,还有顾虑?怕受到打击报复?我一连问了自己几个问号。对老人说:“您老人家莫着急,有话慢慢地讲,我是牛副乡长,今天值班,您不要有顾虑,政府是替村民办事的。”老人大概听我不是本地口音,问我:“你是夏家村的驻村干部牛(副)乡长?”
“是。”
“好!我讲,我叫伍大有,今年八十五岁。”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早些天,夏家村上报红军失散人员的名单中,仿佛有这位老人的名字,而且年龄也吻合,莫非就是他?
随着落实西路军的政策,乡政府正在开展寻找红军失散人员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人民举行“年关暴动” ,县里有很多劳苦民众参加了红军,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打郴州的战斗中失散,有的伤病员又回到了故乡。
我认真听老人讲述,没去核实老人家的身份。老人是用羞涩的目光望着我讲起了自己的遭遇:“我……,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养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们都当爷爷了。现在,我这个大家庭四代同堂,儿孙满堂,可以享清福了。可我那来的福啊!几个儿子为了养俩老,相互推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到头来谁都不管我俩,一拖十几年。我以前还能干农活,女儿嫁在本村,离得不远。农忙时,女婿过来帮忙把田耕好,耙平,责任田里的其它活自己能干,不需别人操心。自己养活自己还没有问题。随着我年岁一年年增大,手脚越来越不灵便,干起农活力不从心。去年又患了场大病,死了,倒也图个清静。可是我生得贱,在老太婆的精心照料下又活过来了,病慢慢地好了。欠下一笔医药费,女儿孝顺,尽力帮着还债。她造孽,拉扯着一群儿女,生活困难,我实在不忍心再给她添麻烦。”
老人喝了口水,接着说:“今年稻谷又黄了,我再没有能力将稻谷收割回来,不得不去找儿子们,他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负责任。我不得不来找乡政府,要告那几个不孝儿子,他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父母生养的,要养父母。”
我听了老人一席话,非常同情老人的遭遇,一股无名火直奔脑门。不加思索,满口答应,明天去处理老人的事。拿起电话,请接线员接通夏家村的电话,请夏家村支书伍奎良、村长伍平安、妇女主任,明天上午十点钟到老人的家里开协调会,并请村委会通知老人的儿子们都要按时参加会议。
送走了老人,在场听到老人讲述的几位乡干部都很恼怒,就马上在办公室里议论开了。中国革命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桎梏,并非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敬老慈幼也要排斥,社会家庭的和谐也算逆动。我们反封建,是要反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文化,封建糟粕,娇枉过正,不能把过去的一切全部都否定。
“文革”,革了文化的命,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都作“四旧”给破了,有的人不忠不孝,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封建余毒进行批判,成为了他们的遮羞布,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成功地开好这次协调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能教育更多的村民,弘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新风尚非常有意义。现在正遇上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穷怕了的村民,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我应当鼓起勇气,去掀开这块遮羞布,让他们丑陋面貌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村民分清是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次日,我吃过早餐,赶到了夏家村。回想起昨天乡干部们的议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村干部十点钟都到齐了,只有老人家的儿子们没按时来。我问刘平安:“你通知过他们吗?”刘平安马上说:“我接到电话,专程去通知过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还不来。”我看老人的几个儿子太没有时间观念,对村支书伍奎良说:“走!我俩登门去请他们过来开会。”村支书伍奎良没想到会叫他去叫老人家的儿子们来开会。有点猝不及防,看看我,站起来,我们一同走出了老人的家。
伍奎良被我叫了出来,不知道我要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一直默不做声。我想讲点什么,欲言又止。俩人同行都觉得挺尴尬的。我到了老人的住房,房子非常破旧,室内陈设很简陋,老人确实只有穿件空筒棉袄过夏天的本钱。当他看见老人的儿子们的住房,一栋比一栋漂亮真令人羡慕时,伍奎良轻声地说:“这些不孝的东西,自己的房屋修得富丽堂皇,可父母却住在破旧的房子中,那可是养育过他们的地方。”他的儿子们完全有能力去修缮,可是他们没去做。我看了也不是滋味,虽没讲话,脸色却变了,也在心中咒骂:这些不孝的东西,良心让狗叼走了,父亲没换洗衣裳,连件衣服都不给买,那怕是随便给件自己穿过的旧衣,给老人作为换洗衣服,也算他的良心尚未泯灭。
协调会开始了,老人家的儿子们个个自知理亏,无地自容,有的低着头一个劲地抽烟;有的下意思地玩手指头;他们就是不敢抬起头面对众人,不敢有半句绞辩之辞。老人家理直气壮讲了自己的几点要求,他的儿孙们不敢再相互推诿,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伍奎良支书讲了几句话,请我发言。我看问题解决得顺利,本不想讲话。但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全乡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局面,夏家村反映出来的问题,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普遍认为:生了男孩家族里增加了势力,家庭增加了劳力,母亲在家增加了权力,所以敢于冒着风险超生;有人用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来对付乡干部。但是,像伍大有这位老人生养了五个儿子,老人连换洗衣服都没有,晚年他生活无着落,儿子们都不管,生病时儿子们不理,都只顾过自己的小日子。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想找机会要说几句,今天机会来了,把想要讲的话通通说出来,我放开了嗓子大声地说:“大家都讲要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可眼前的事都看到了,老人家有五个儿子,在这十几年里,他们尽了什么孝!老人家名叫‘大有’,希望老来不但‘有’,而且要‘大有’,可是养了这么多儿子,老人家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还要为吃饭在风雨中劳作,连多余的换洗衣都没有。俗话讲:‘养不教父之过。’”
我对着老人说:“您老人家养育出一群不孝的儿子。”
老人家听到我的话,脸色变了,立即吃力地站起来,向我鞠了个躬“是!我的错,我的错,养了些不孝的儿子,父之过,父之过。”我看到老人家尴尬的模样,心里在想,中国人是很要面子的,不能妄言,不能太偏激了,人家的孙子的个头都有我这样高了。
农村召开协调会,调解家庭纠纷,负责调解的人,一般都以“和事佬” 的面目出现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不痛不痒批评几句,其目的是顾全各方人的面子。我在讲话时是否也要平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也当回“和事佬”,照顾他们的面子呢?否则,自己会激起村民们的义愤,陷于孤立的境地。又想自己不是本地干部,在这儿工作两年,不必有那么多顾虑,胆子又大了些,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应当去鞭笞,应当让几千年的文明精髓传承下去,不管有多大的副面影响,豁出去了。
又接着说:“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非常艰难,都想养儿防老,就是多子多福的思想在作祟。大家都看到了,眼前这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就生养了五个儿子,五个啊。”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松开五个手指,扬了扬,用这种手示来加重语气:“在十几年里,儿子们为赡养父母相互踢皮球。儿子不赡养老人,养了又有什么用。”又将手用力地收回来:“谁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从这件事说明了,生男生女都一样,是没有区别的。他真有一位孝顺的好女儿,这些年来就是他的女儿,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也为她的子女作了榜样,她会享到子女们的福,她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女儿好!女儿好!她是父母的贴身棉袄,暖了老俩口的心。”我又用严肃的目光扫了老人家的几个儿子,又盯着年过花甲的老大:“你也会老的,带了这个坏榜样。你也老了,不能动了,子女们也学着像你那样,让这种故事重演,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我看你是自作自受!欲哭无泪!中国有句古话,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就是讲给你们这些人听的。”会场上鸦雀无声,我讲完话后,心中有种从未有的畅快……
协调会上的发言,伍奎良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又会怎样想呢?散会后,我与伍奎良等人同行,看样子我的发言对他有点促动,在回去的路上,他还是一直默默无语。他会不会认为我在敲山震虎,戳他的脊梁骨呢?的话火药味特浓。根本不顾及他人的面子。他也有个性,里面还会暗藏其它的用意吗?很可能是有所指的,这次计划生育工作,村里确实做得太差了,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可他是在给了自己的机会,在基层工作几十年里,为挽救一个同志采用的常用手法。这小子也不是那样简单的角色。先召开个支委会,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不久,伍奎良邀请我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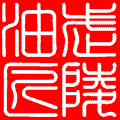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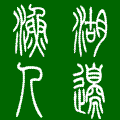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