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他乡>>——(14)打劫
在纽约市的新闻和报纸上经常有中国来的外卖郞被劫杀的事件,他们大都是来自福建的小青年,一般是在自家开的外卖店里做工。他们被劫杀基本都是一个模式: 由几个十几岁的黑人打电话到外卖馆,要几样菜。送外卖的人就会进入这些打劫团伙的圈套。最可恨的是这些团伙不但抢了外卖郎的饭菜和钱财,最后还要杀人灭口。在纽约,做外卖这样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我在周围的认识朋友中见到过两起打劫事件。
在我们十六家房客的二楼上住着一位从南京来的小伙子, 他大概三十五、六岁,瘦小的个子,他走路像女人,操一口软软的吴语,能说会道,就是一个奶油小生,这栋楼的人都管他叫“周小姐”。小伙子对这样的称呼并不介意。他会一点英文,在曼哈顿的一家中餐馆做服务生。餐馆服务生是很辛苦的工作,早上十点半之前就要到餐馆,晚上要到十一、二点才能下班,坐地铁回到家往往是半夜一、两点了。一个周末的半夜,周小姐下了班,出了地铁站往我们住的楼走时,突然被一黑人用一硬梆梆的家伙顶住了腰,要他交出身上所有的钱财。他吓得没办法,把自己身上带的背包交给了抢犯,抢犯拿起包就飞跑了。这时周小姐才想起除了自己一星期的工钱外,护照也在那个包里,没了护照那可是非同小可,这时他用英文拚命地喊起来:
ROBBER!ROBBER!(抢劫)
正好这时有一辆警车开来,警察问清了情况,很快在附近抓到了那个抢犯。警察把抢犯和周小姐一起带到警局里录了口供后,把背包还给了周小姐。早上周小姐回来后,整栋楼的房客都去看他,打听情况。只见周小姐坐在床边两腿一直在发抖,站不起来。我们安慰他说:这是你被抢了,还追得回来,如果抢的是我们这些不会英文的,那可是干瞪眼了。周小姐吓得有一个星期没敢去上班。后来他就去了外州的餐馆打工了,外州的中餐馆,员工一般都住在附近,相对安全一些。
看到周小姐被抢后一直很害怕,后来我老板秦太告诉我:像你这样不会英文的,最好是在脖子上挂个口哨,遇到有人打劫时,就猛吹哨子.这样会引起行人和警察的注意,也许会有帮助. 后来秦太给我的哨子,一直陪伴了我很多年.
不是每个人都有周小姐那么幸运。
王太是个从马来西亚来的新移民,五十来岁,个子矮小,会说中文,她靠理发为生。她的收费要比理发店便宜一半,我们这些穷打工的人都是她的顾客。王太把理发工具放在小旅行箱里,如谁要理发、烫发只要打个电话给她,她就会拖着小箱子上门服务,很方便。可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挣辛苦钱的中年妇女却死在抢犯的刀下。
一天晚上大约在十一点左右,王太从发廊打工完回家(没有客户打电话时,她就在发廊做小工), 在离家门口只有两条街的地方,被一抢犯拦住,要她交出身上所有的钱财。王太当时只有五十块钱,这是她辛苦一整天的所得。她紧紧地保护这五十元钱,不甘心被他人夺去。抢犯下了毒手,两刀把王太捅死了。可怜的王太为了五十元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后来警察局专程到华人居住区,召集新移民开会,提出忠告:第一,出门在外,不要带很多现金在身,也不要把大额现金留在家里,一定要存入银行;第二,万一碰到劫匪,赶快把钱交出去,切不可因小失大,为了区区几十元钱而丢了性命。
我家里也曾两次被小偷光顾。一次是我在新泽西州上班时,我先生和弱智儿子在家。小偷撬开地下室门进来,然后从一楼到二楼转了一圈后,走了,一点东西也没偷。后来朋友笑话我们,这小偷应该留下二十元钱给你们。这样一无所有的家也值得破门而入?
第二次是在周末,晚上十点钟,我从打第二份工的长岛开车回家。一进门,就发现整个的后门被人从外踢倒在屋内地板上。我吓得急忙叫醒正在睡觉的先生,他爬起来一检查,还是没有丢任何东西。朋友们再笑话,你家应在后门上贴一告示上面写:
"尊敬的小偷先生:很对不起,我家比你还穷!"
中国有句熟语:一字不过三。我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小偷会第三次光顾我家。
这是我家的前门,从外面看这栋房子像模像样的,其实里面啥也没有.什么原因?以后会写到的.
曾挂在脖上的哨子,我一直保留着.
<<在他乡>>----------(15)跑
在国内时经常听到看到一些乡下来城里的民工,因急诊进医院治病,病稍微好点,有的人就会选择一个时机一跑了之。因为他们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没想到在美国以“跑”来逃避医疗费的办法被很多没有身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用上了。
刚到美国,我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万一哪天病了可怎么得了?一位来美国多年的老前辈笑我是杞人忧天,他告诉我,没有医保没关系,真正大病来了,往急诊室一送,美国讲究人道,定会救治的。病好了就一跑了之,只是要记住不要在医院留下真实姓名和住址。
我们十六家房客里的黄先生,来美时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一日他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下室不省人事。大家慌了手脚,会英文的孙教授赶快打电话求救护车,其他人七手八脚地将黄先生抬出地下室。这时有经验的王先生马上提醒大家,赶快把黄先生身上的一切证件拿掉,并再三嘱咐黄太太到了医院后,一定要胡编乱造一个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两天后黄先生没事儿一样地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在地下室休养了三天,又去洗衣店打工了。后来黄先生拿到了绿卡,申请免费医疗保险,经常去取一些免费的保心脏的药吃。前些日子我在街上碰到黄先生,已经七十几岁的他,还在那同一家洗衣店打工。他告诉我这家洗衣店已经四换老板,但是每一任新老板都留下了他。因他做工作认真踏实,他的心脏病一直没再复发过。我佩服美国的医疗技术,也佩服黄老先生的吃苦耐劳精神。
这个“跑”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但也有人出了岔子。一天我们的老乡毛先生阑尾炎急性发作,不知道他老人家是疼糊涂了,还是没人告诉他可以给假姓名。他在医院登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及地址,结果几千元的医疗账单寄上门。毛先生急了,请了一懂英文的朋友帮他写了一封信到有关部门,讲述自己经济困难,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最后判决是:毛先生可以每月付28元,要十几年才能付清。这样的分期付款对病人来说是一条出路,因为不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我母亲在美探亲其间也突发过心脏病,我弟弟住在小城市,大家互相都认识,不能用假姓名和地址。等医院八千多元的账单寄来,弟弟也是申请了分期付款,每月付一百来元,大概要七、八年才能付清。
我自己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大“跑”,因不是小“跑”。所以将在《大难临头》篇章里详细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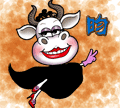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