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尸记】
71年寒冬的一天深夜。刺骨的北风直往脖子里灌。我踩着一辆(带回轮头)板车,依照约定,来到一家医院停尸房的墙外。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忽闪着点点昏黄的灯光。寒风阵阵袭来,我将面对死亡与恐惧。
与我约定的是个农民。那是我从搬运队干活回家的路上。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蹲在墙角掩面而泣,旁边放着一个旧布包袱。天气寒冷,偌大一条街道看不到几个行人,无人问起这蹲在墙角的中年汉子。我看着眼前这人好一阵,也找不到他伤心的答案,他不是流浪汉,也不象病人,遇到了伤心事?我对着他喊:“么子路咯?”,俨然一副包打天下的豪气。虽然我比这汉子年纪小了十多岁。听到我的问话,他抬起头,更是泪水涟涟,又将后脑勺使劲往墙上碰。其状,定非一般之事。我慌忙下车,凑到跟前轻声问:“老哥有事对我讲。”他摇头又摇手,似乎不相信面前的年轻小伙,又看我的装束,一身补丁衣,腰缠一根长布绑带,象个下力之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我这模样,多了几分信任。于是,他说自己姓陈,家在湘潭。早些天陪他哥来长看病,未曾想他哥不治死亡。
原来,上年的12月,正是寒潮来临。他哥挑了担小菜进城,碰上管市场的,将菜没收;他哥是个血性之人,因不服而与人争斗,寡不敌众,还被关了一晚,回家后一病不起。眼看年关将至,全家凑些钱让老二送哥来省城治病,医诊为内出血。前后五天,一命呜呼。老二举目无亲,钱也所剩无几,通讯又不便,情急之下,没了主意。一个人靠在墙边着急,恰好让我碰上。那段时期,正是我插队安乡,第一批招工回到长沙,因海外关系,将要遣送回安乡之前的一段日子;没有了工作,在社会上干些苦力谋生。想到我与这个农民一样,徘徊在十字街头,一种同情由然而生。我问他:“要帮忙啵”?他说:“想回家还得把我老兄带回去”。“怎么带?你医院冒结账,还要汽车才回得去呀!”一句话说到了他的难处,他竟又哭得象个泪人,“哥啊!娘啊!”地嚎起来,搅得我心里发慌,一时没了主意。想走,又不忍心,我不知如何是好。
天色渐渐黑下来。看他可怜,我将他带到家里,跟我娘说明来由,我娘叹气,让先吃了饭再说。饭吃到一半,我猛然冒出个想法,跟他商量了一阵,这汉子居然没了愁容,只说“怕不行吧”?那眼光带着几分疑惑,思前想后,终于下了决心。赶紧吃过饭,让他先去医院。于是就有了故事的开头。
我将板车停在墙外的斜坡高处,站在板车上,双手扶墙,探头往里张望;墙那边是个天井,停尸房内一盏昏暗的灯光下,见那汉子正在跟他哥哥穿衣,一阵呜咽声隐约传来。我向他发出拍击声,他回头会意,赶忙搬了张条桌出来,放在墙根下,我示意“.快!快!”,只一会,这汉子已经拦腰摞着他哥站上了条桌,我伸手与他同时发力,他顶我提,他哥已横上了墙头。我一手拽住他哥的衣服,側肩顶着尸体伴墙下滑,那尸首耷拉在我的肚子上,一阵寒气袭来,两条腿不停抖动,不知是恐惧还是车子不稳,屏住气息折腾了好半天,却放不下尸体。等老二翻墙过来接着他哥,我才松了口气。两人赶紧拖车就走,一阵小跑拖到大马路上。四顾无人,老二从包袱里翻出一条白布单,盖在他哥身上。直到这时,我的心脏仍在乱蹦,似乎做了亏心事,口中发干腿发软。当初在老二面前的豪气也少了三分。事已至此,硬着头皮往下走罢。
已是子夜时分。空中弥漫着阵阵寒气,气温越来越低,点点雪花飘落在脸上冷飕飕的。两个活动的生命一前一后拖着车子往前赶路;他哥直直地摆在车上,身体随着车子的颠簸不停晃动。白雪渐渐盖上了他的全身,静静地,悄无声息。那是一种以白为原色进入眼帘的哀伤。死者无言,任由摆布,生命的张力早已消失。在寂静与永恒旁边,还有我与老二脚踩雪地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方昭示生命的存在。
过了易家湾,还有二十多里路,两个人已显疲态。汉子跟上我,用一种感恩的口吻对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我没吱声,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天色渐渐泛亮了。忙活了一夜,肚子也饿起来。汉子告诉我,前面已到湘潭地界。人忽然从机械地不停走路中清醒过来,两人都在看路边的店铺。一家冒着热气的铁皮棚子正在前边,赶忙停下车。两个人争着掏钱,我说,你看着车,将你哥整理一下。汉子依言。我从铁皮棚内端出两碗面,用筷子穿着十个油炸馒头,回到车前与他大口吃起面来。两只碗很快底朝天,再找馒头却是放在他哥盖着的布单上,心里一阵发怵。再看老二,却是抓起馒头就吃。血浓于水,到底是兄弟。饿到极处,我也将就填饱了肚子。送碗时,铁棚里的人自然看到了我们,那车上一动不动,用布单盖着的死人,让人不寒而栗。店铺的胖子接过碗筷,将筷子朝路边的坎下一扔,低头“呸”了声,我猜可能是吐晦气。于是,两人加紧赶路。路过一小店,我提醒他买挂鞭炮,他照办了。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四周一片白茫茫的田野。偶尔有一两个农民迎面而过,都朝车上张望,顺着那种眼神,见车上不停晃动的老兄,头已露出白布单,满头满脸盖上了雪花。他模样并不难看,只有种冰冷的感觉。一个活人这般颠簸,怕早已消受不了。没有了生命,就任由摆布,一了百了,再无所求。
拐过一条田埂,前面有一线房子,稀稀落落有茅草屋,也有几座矮砖房。墙上白灰刷的标语分外醒目:“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铲除资本主义尾巴!”
我问他:“快到了吗?”“到了!到了!前面就是”。家门近在咫尺,这汉子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又掏出火柴,抖抖索索点燃了鞭炮。一阵划破天穹的噼啪声,将那些房子里的人震出来,有人朝这边张望,又见一群人往这边跑来。突如其来的变故,搅乱了乡村的宁静。几个主事的忙着卸下尸体,一堆人早已哭成一团。
一处并排五间的房子,是两兄弟的家。堂屋的地上,老大躺在一块门板上。昨晚到现在,我才看清这张陈姓农民的面容。一层冰茬在前额处泛着白光,短发,有个鼻孔内塞着一团带血的棉球。我默默地转过身。
老二在与一些人说话。我向他打招呼,示意我要走了。冰天雪地,我还有几十里路途,要赶回家还车子哪!一会,他带着老的小的一家子,忽啦啦跪倒在我的面前,老爹举着一根纸烟,噙着泪水向我道谢。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撼!那场景实在让人心酸!我不敢想象,这一家子往后的日子将会怎样?弄得如此凄切的起因,竞然是一担小白菜。呜乎!?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可是,我依旧沉浸在凄凉和悲戚中。想到不久我将再次遣返安乡,一阵深深的忧愁和绝望涌上心头,泪水终于涌出眼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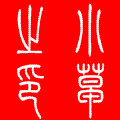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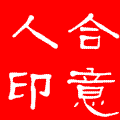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