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的回乡手记,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今年安乡知青集体返乡,我无法参加,我用这种方式与插友们同行,并我纪念我的下乡40周年。意外的是这文在安知网上让我找回了我的老友。
贴到茶座,是因为当年我们学校下放到安乡的极少,我的同学现在应该散布在湖知网中,希望能通过此文在茶座这块“公共”区域找回多点的老同学。希望我能如愿。谢谢“茶座”这个平台。
故乡?啊,故乡……
——我的回乡手记
从下乡的地方回城以后,前途命运的大事塞满了脑子,从来没有去想过哪怕一丝丝关于“故乡”的话题。“故乡”,无非是指一个人的落生地,那对人有什么要紧的吗?象我们这代人,都是落生在医院里,最先触摸我神圣的皮肤的,是那个接我出世的护士。连她我都不认识,还有必要去认什么“故乡”吗?再说了,到我从乡下回家的日子为止,前段人生也并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那小脑袋要想记出点什么事情来,还得歪半天想想那是发生在哪座城市哪个学校。所以,“故乡”对我来说既无意义也乏味得很。
后来下过乡后,常听人说起“XX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样的说辞,更觉得好笑,觉得矫情,我就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除非跟人开玩笑。
第二故乡!我对那个献出了自己金色年华而一无所获的地方毫无眷念之心。除了夏日的火冬天的寒,插不到岸的秧薅不到垅头的草,还有什么呢?
那座水乡小村回忆起来永远是晒得发白的路面,永远也长不粗的细树杆挂着永远稀疏的树叶,什么时候才能在浓荫下喘口气?即算偶有忆起,也只是听到第一声打谷机响起时的心惊胆颤,太阳渐渐变得最炙热时的腿肚发软,多少次看到白金色的太阳我心就发慌,顶着烈日踩在烫腿的水田里的日子实在难熬,用下一代人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在向自己身体的极限挑战。
难道这就是别人老喜欢挂在嘴边的温情脉脉的“第二故乡”?可我从来就想压根把它忘掉。我也确乎很成功地把它忘掉了。然而,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是把它连同我自己一块忘掉的。
大约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位老友从境外回来过十一。也许是在外边飘泊久了,看腻了灯红酒绿,她突发奇想要找个乡下玩玩,而我认识的乡下只有我的“第二故乡”。
“既然咱俩都找不出乡下亲戚,那就到你的生产队去吧。”她说。
于是,我邀了邻大队的一个知青,开始了我们的回乡之行。对这位远归的朋友算是下乡猎奇。
当年我们离开安乡时是坐着船出来的,这里不知何时通上了汽车。汽车行驶在陌生的公路上,扬起一路尘土。这感觉有些新鲜,在我的知青生活里从没有过,所以一点也引发不出旧日印象。对这种不怀期待的出行我经历很多,平常居家之日,就喜欢一个人尝试各条公汽线路:从起点坐到终点。有时只是为了找点头脑一片空白的感觉,有时是好奇平时不曾去过的终点站是个什么模样,有时是想弄明白某条线路在什么地方突然改变了方向?这种别人看来很无聊的出行我却常常乐此不疲。这次坐在赴安乡的长途车上,也是怀着这样的无聊心情。我并不期待那个“温情脉脉”的地方,只是又一次身体的位移而已。
车到县城,有同学在街口接我们,她一直留在那儿,现在做了某政府部门的领导。相隔了二十年,居然模样一点儿也没变,同样的手势,同样的笑容,虽不漂亮但同样青春焕发的脸庞,让我连感叹人世沧桑的机会也没有。县城里特有的交通工具人踩三轮载着我们穿街过巷,尽管同学祥尽介绍县城的旧貌怎样变成新貌,但无奈旧貌就印象淡薄,新貌也就完全陌生了,丝毫也唤不起我心内来自遥远岁月的回应。
进了她位于某局内的宿舍,俗套地递上见面礼,俗套地在她的领地小小巡视一番,突然,我一眼扫到了卧室中的一张硕大无比的硬板床,身体的某根神经猛然被拨动了一下,知青世界的某个角落被掀了出来:那是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吗?寒天冻地,不准回家,没有取暖材料,就是在这样一张硕大的硬板床上,横躺着两个队我们5个知青。低矮的茅屋外雨雪淫淫,风在低空呻吟。那一夜,我们一起想家,一起想曾经的校园生活,童年的玩伴,少年的同桌,一起伤感,一起莫名其妙地大笑,紧紧挨在一起互相取暖,最后一起进入忧郁而甜蜜的梦乡。。。。。。有一个脑袋在那个风雪夜梦见了冲天大火,然后五个脑袋又一早解析这个充满“财气”的梦。清晨的寒气渗入被子,这个硕大的硬板床却被一个火光冲天的梦境温暖着。直到近中午有人下得床来,走到门口惊呼:“真的!真的!有财!有财!”五双眼睛又一齐瞪着一只躺在门外的白羽毛阉鸡,多半是它昨夜没找到谁家的窝门,活活冻死在我们家没门页的门槛外面。一个伟大的梦——那天我真的相信了美梦能成真!一个意外丰盛的春节!
同学执意把我们送到已随军复员到县医院的妇女主任家,她早为我们备好了食宿,新居里整整一层楼房供我们三人享用。尼龙蚊帐,发亮的化纤被面,釉面砖闪着寒光,站在这个伪豪华的卧室中,突然觉得有几分滑稽,有一些“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我很抗拒这种感觉,虽然这次回乡我并不想打开心门,我不准备把那段年月里的情愫在忘了二十多年后再重新接纳它,但这种贵宾驾到的感觉更不是我的预期心态。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那张大床,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于是我坚持要回到同学家去。是想重温当年抵足同眠的旧日时光?幸好同学“客气”地拒绝与我们同眠一室,那张能睡5个人的大床上,只留下了我们三个回乡和猎奇的人。一夜难眠。这样很好:没有叙旧,没有回忆,心如止水,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明天,明天,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这一刻,我甚至想明天回去。
等到“明天”降临时,我想我还得咬咬牙,尽一回地主之谊,不能让那位猎奇的朋友太失望。再说,我还带了这多床单枕套,总得随便送些什么人吧。
一早起来,租了辆的士,用这种局外人的姿态返乡,很合我的心情。
车行了有一段路,前方闪过一些被树枝分割的白色光点。我很奇怪的盯着渐近的那些闪烁的碎片,到底是什么在阳光下闪光?车在一个豁口突然开朗,扑入眼帘的是一大块水面,象镜子一样反映着天光。珊珀湖!?是珊珀湖!——这是从我记忆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名字。没想到我忘了它们20多年,它却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让司机开慢一点,让我看看这一池忧伤的湖水。二十多年前一个阴沉沉的天,我们就是从这里下船,登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站。往日的回忆便从这湖水中一个劲儿的翻腾涌动出来,我连自己也不明白何来的幸福激动,竟渴望冲出那个“局外人”的外壳,回到我曾经生活了五年的村庄里去。
那里有我的茅草房,有我走过无数次的田埂;我曾在门前那条深水渠边学着村民高高地举起棒棰拍洗衣裳;我在那片田边的水塘里挑过水,扁担一闪一闪的节奏,当时令我充满自豪感;我曾静悄悄地聆听过我种的黄瓜悉悉索索生长的声音,它们顶着萎花结出的乳瓜那么嫩那么小,象新生的婴孩令我感动得泪花盈眶;日暮收工,太阳西沉时分,远处常飘来不知谁人在高声唱着的《三套车》,那深沉苍凉的旋律,勾起无尽的关于理想的幻灭,对往日生活的深深眷恋,对远离的亲情的渴想,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关于这点,现在是没人相信的,但我们真的就有那样的忧郁);我听见了我蹬着水车伏在横杆上喊着“哟嗬~~嗬~嗬~~~”的遥远的回音,那几乎没有旋律的音调,长长的颤抖的尾音说不出的惆怅,象幽灵一样向寂寞的田野上飘散,好象在寻找永不存在的归处;我曾多少回站在窗口对着屋后的那片田野聚目凝神:初春的紫云英一直开到天边,我随着那条在朝阳下晶莹闪烁的花路笔直地想到了长沙:破碎的家,天各一方的亲人。我记得是那片紫云英给了我安慰:你不会孤单,我们都在这儿为你开放;初夏,紫云英走了,她们变成了满满一原野的新绿,簌簌喧响,象海洋一样辽远,有时能看到几只白鹭上下翩翩翻飞,款款行走在那片无边的绿色中,美得令人叹息。那一刻曾令我坚强:这世界到处都美,哪儿不能为家?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只要有天,有地,有太阳……那就该象白鹭一样悠闲洒脱地活出美的极致;到了秋天,能闻到稻花的清香,花开过,结穗了,一阵阵带着湿气的谷浆的香味随风入室,那片被风抚弄的稻原沉沉地一摆一摆,象丰腴的孕妇,象步履蹒跚的老人。夜深人静,我似乎听到沉甸甸的稻穗互相碰撞的声音。啊,那个低矮茅草屋檐下的小小窗口,我不该忘了它!透过它我看到了生命的旅程,我曾站在那窗口边对自己说:同为生命,我也会有自己的姿态和色彩,我也会活到“沉甸甸”的那一天。
这些,都是延续我生命的血液,我怎么能说忘就把它们忘了呢?长在树上的一片叶子,它能否认老树盘根错节的根须吗?
我有了些心虚的感觉,那个自信的“局外人”一下不存在了,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情让我惴惴不安。
我让司机停了车,决定步行进村。也许这一刻我想到了跪乳的羔羊。走吧,低着头走,那前面是我的衣食父母。在那个阶级仇恨焚烧人心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平等的温暖,父母前途未卜,是他们把我领入了重新宁静的生活。出工前,他们帮我磨锄;下工后他们教我往冒浓烟的灶膛里吹火筒;他们鸡窝里的公鸡母鸡,很多都是我的小鸡们的父母,那些小鸡曾伴我渡过了孤独的知青岁月;是他们把我教成了插秧高手,常常在下田前,队长一声喊:“小Z,下第一YI”。下第一YI可是个很高的荣誉,插手们都知道,第一YI是不容易插好的,一来田垄弯弯曲曲,牛是没法犁到的,没犁的生土很难稳秧,二来插第一YI者必是快手,且须又匀又直,以给后下YI者定好坐标。在那声“小Z,下第一YI”的呼唤中,我又找回了失落的自信。并且我坚信,它一定丰富了我今后的价值观:哪怕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仍然非常期盼那一声“小Z,下第一YI”。那是一种心灵超脱世俗物欲时的轻松喜悦,它让我相信在物化的生存之外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值得追求;在我身心疲惫的时候,也是他们给了我快乐,还记得一次插秧时突遇大雨,大家高兴地躲进学习室,也只有仰仗老天才能舒展一下酸痛的身子骨。我在心里默祷:让我多憩一会,千万千万别把雨一下倒完。这时只听得那生产队的团支书仰头大喊:老天老天,你可要细水长流啊!这个知青式的幽默让我开怀大笑,笑到雨停。一边笑一边涌上一股酸楚:这磨人的日子到哪才是个尽头?
知青生活就是这样——一边苦着,一边快乐着!一边忍着,一边期盼着!
(续后页)
















 看罢英友此文,两点感受:原生风景惹人醉,农民生活心酸泪。看来,建设社会了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呀!老知青,回故乡,除了英友文,再也无文章,呜呼!
看罢英友此文,两点感受:原生风景惹人醉,农民生活心酸泪。看来,建设社会了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呀!老知青,回故乡,除了英友文,再也无文章,呜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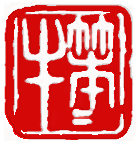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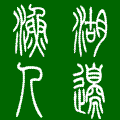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